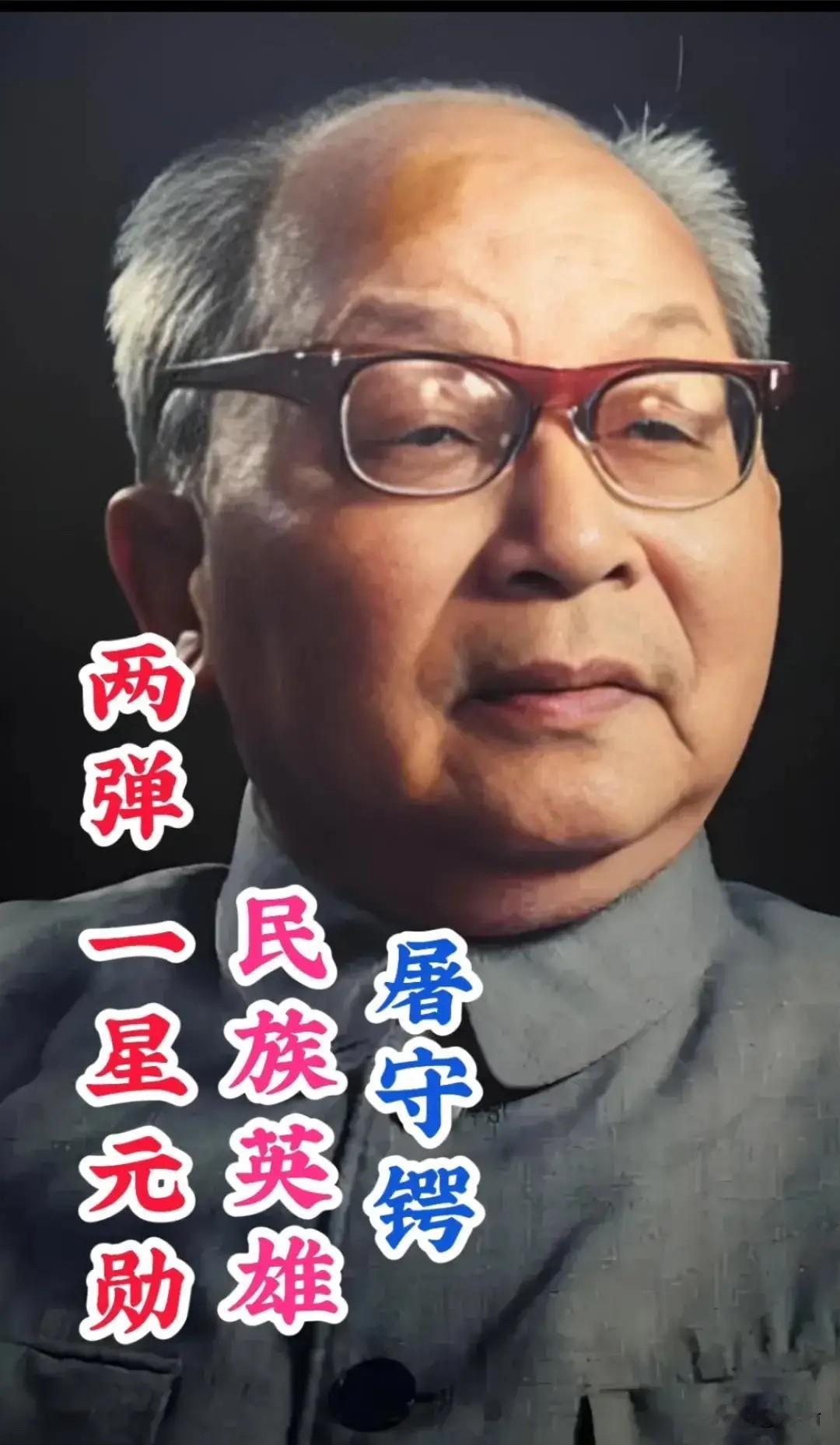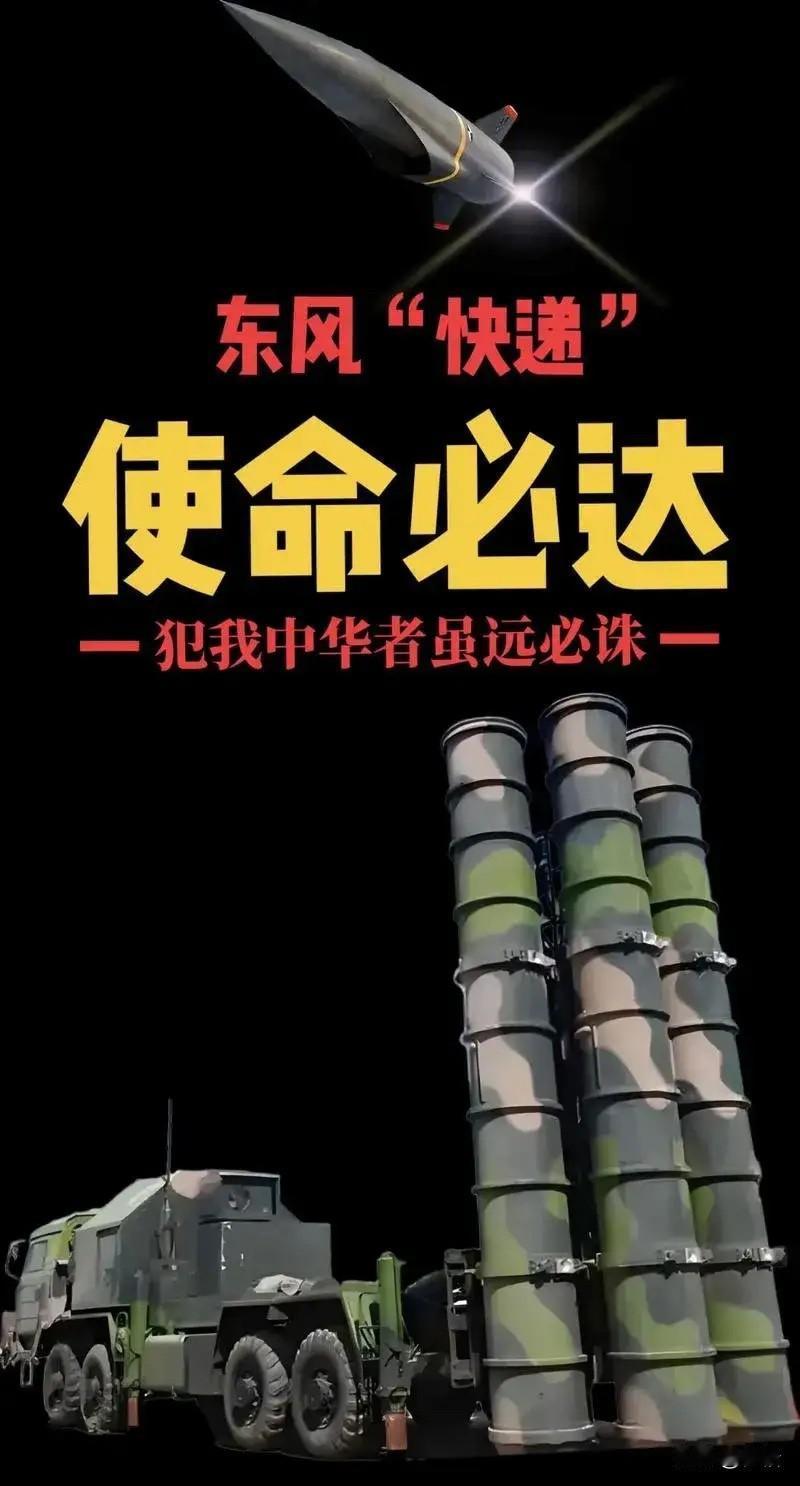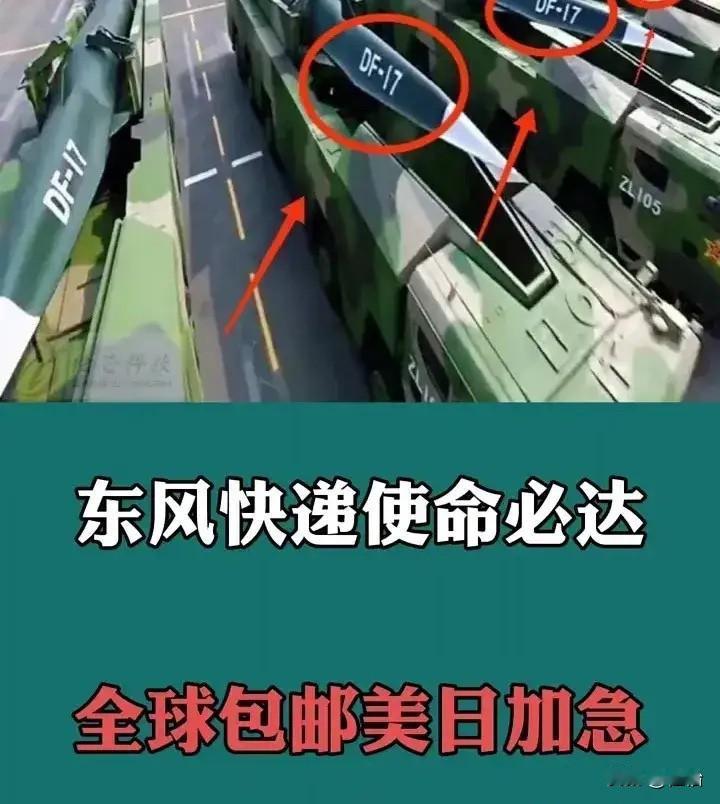四分钟抵达日本东京,十六分钟到达英国伦敦,半个小时即可横扫整个星球,东风快递使命必达,绝非浪得虚名。 而且一旦发出则无法拒收。 谁都知东风导弹足以让世界闻风丧胆,但却很少人知道东风导弹背后的这个男人,他就是两弹元勋功臣、中国洲际导弹之父,中国航天四老之一屠守锷。 屠守锷这辈子,好像就没为自己活过。1917年出生在浙江湖州,家里是书香门第,可他偏偏不爱笔墨爱机械。十来岁时看报纸,上面印着日军飞机轰炸中国城市的照片,他攥着报纸跟父亲说:“将来我要造飞机,把这些侵略者赶出去。” 这话不是少年意气。1936年他考进清华大学航空系,卢沟桥事变爆发那天,他正在实验室画飞机图纸,警报声划破校园,同学们跑着躲防空洞,他却盯着图纸发呆——纸上的飞机还没翅膀,国家就已经被敌机炸得千疮百孔。后来学校南迁,他跟着一路颠沛到昆明,在西南联大接着读书,煤油灯下画的图纸,边角总沾着汗水和泥点。 1941年,他争取到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留学的机会,学的还是航空工程。那会儿美国的航空工业已经甩开中国几十年,实验室里的风洞设备、精密仪器,都是他在国内想都不敢想的。导师很欣赏他,说只要留下,能给他最好的科研条件,甚至承诺帮他申请美国国籍。 屠守锷却摇了头,1945年拿到博士学位,收拾行李时只带了三样东西:几本专业书、一把计算尺,还有一张从报纸上剪下来的中国地图。 回国的船在海上漂了两个多月,他在甲板上反复看那张地图,手指划过西北戈壁——他听说国家要搞火箭导弹,那地方将来肯定用得上。可真到了动手的时候,难住他的不是技术,是没条件。 1957年他调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负责导弹总体设计,办公室是废弃的旧仓库,桌子是用木板拼的,连像样的计算设备都没有。 同事说他有个怪习惯,兜里总揣着个小本子,走路、吃饭时想到什么公式,立刻掏出来记,因为那会儿连台像样的计算机都没有,很多数据全靠手算。 东风一号导弹研制时,有个难题卡了三个月:发动机推力总不稳定。屠守锷带着团队住在试验场,天不亮就爬起来看数据,晚上围着煤油灯讨论,有人累得趴在桌子上睡,他就用凉水擦把脸接着算。 有次试验失败,导弹刚升空就偏离轨道,炸成一团火球。现场没人说话,他蹲在残骸旁边,捡起一块碎片看了半天,突然说:“推力向量控制有问题,明天改方案。”语气平静得像在说天气,可同事发现,他握碎片的手在抖。 1960年11月5日,东风一号发射成功那天,他站在发射架旁,看着导弹冲上云霄,没像别人那样欢呼,只是掏出兜里的小本子,写下“首飞成功”四个字,笔尖划破了纸。后来有人问他当时在想什么,他说:“想起当年在西南联大躲轰炸的日子,现在咱们也有能飞的‘硬家伙’了。” 东风五号洲际导弹研制,才是真的硬仗。1977年他担任总设计师,那会儿国外对我们技术封锁得死死的,连个参考数据都拿不到。有次为了确定弹头再入大气层的防热材料,他带着人在实验室烧了上百种样品,胳膊被高温烤得起了水泡,还笑着说“多烤几次就知道哪种经烧了”。 1980年5月18日,东风五号从酒泉发射,横跨太平洋,准确命中预定海域。消息传来时,他正在吃午饭,端着碗的手停在半空,眼泪掉进了碗里——那天的米饭,他说比任何山珍海味都香。 你知道吗?屠守锷晚年接受采访,记者问他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是什么,他没提东风导弹,只说:“我回国那年,国家连像样的导弹图纸都没有;现在,咱们的东风能绕着地球跑。”他一辈子没给家里挣过什么“体面”,儿子说父亲的工资大半都买了专业书,家里最值钱的就是书柜里那满满当当的资料。 从战火中立志造武器保家卫国,到用一辈子心血让中国拥有洲际导弹,屠守锷们图什么?图的不就是让国家不用再看别人脸色,让老百姓能睡个安稳觉吗? 当一个人的理想和国家的命运紧紧绑在一起,这样的人生,是不是比任何名利都更有分量?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