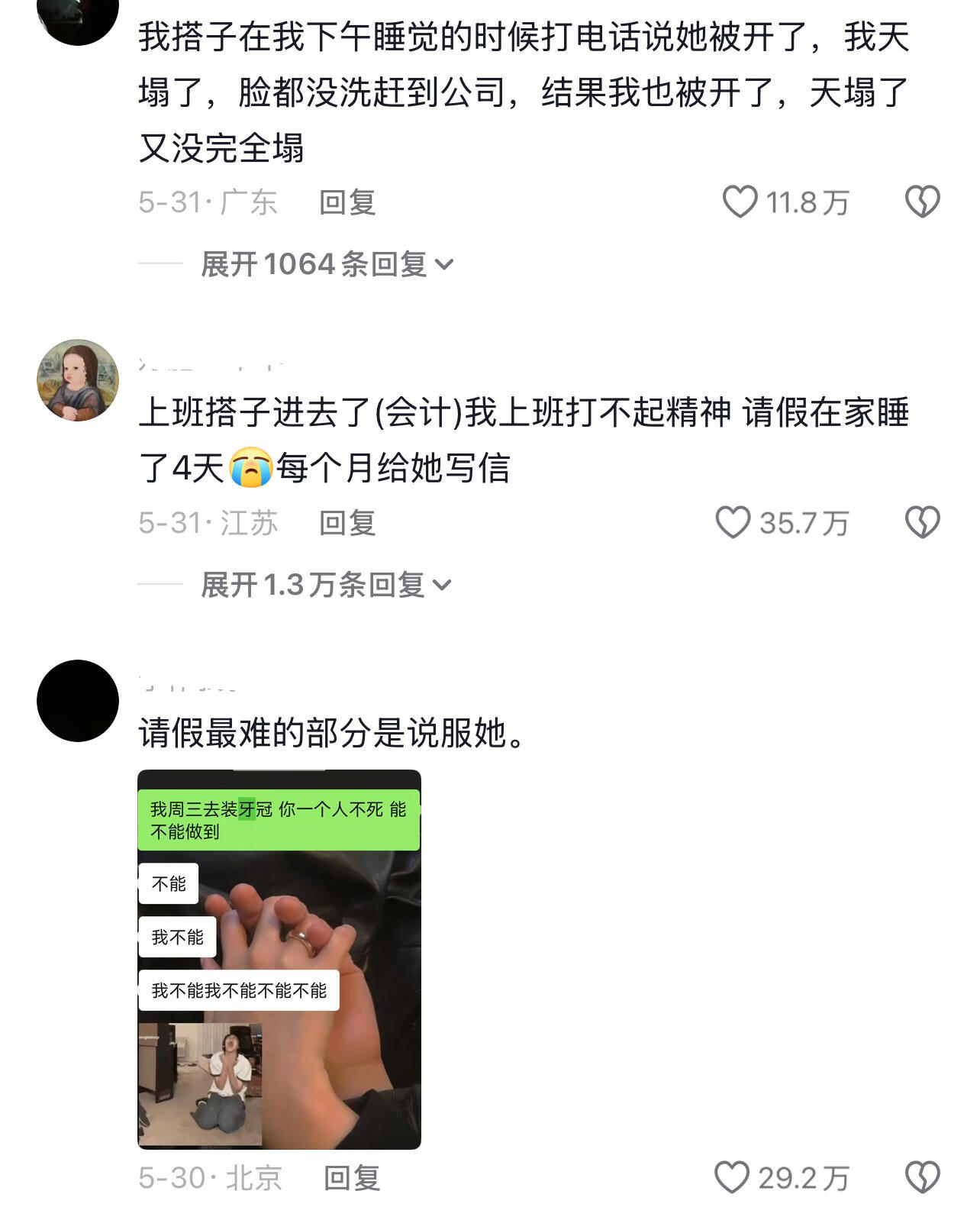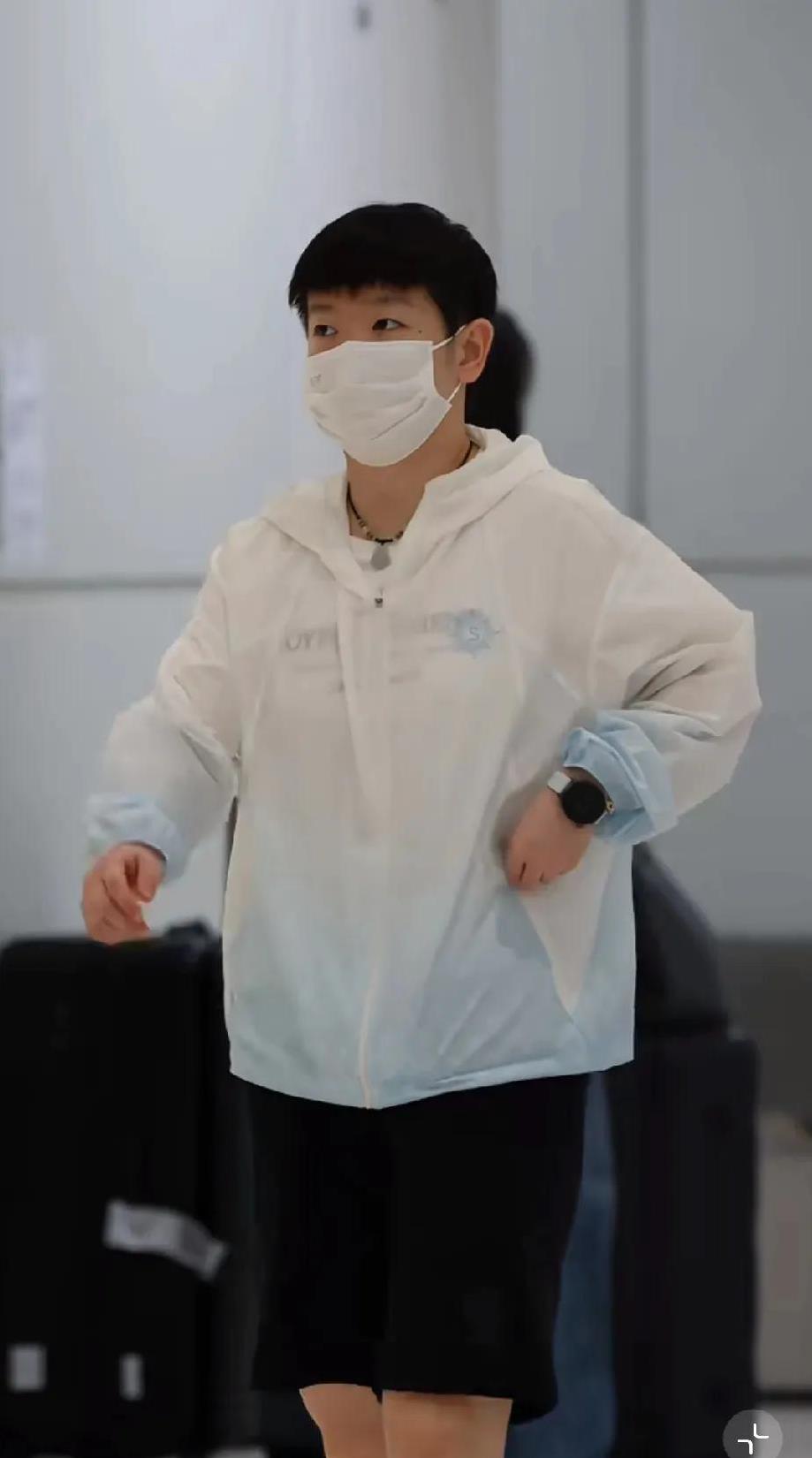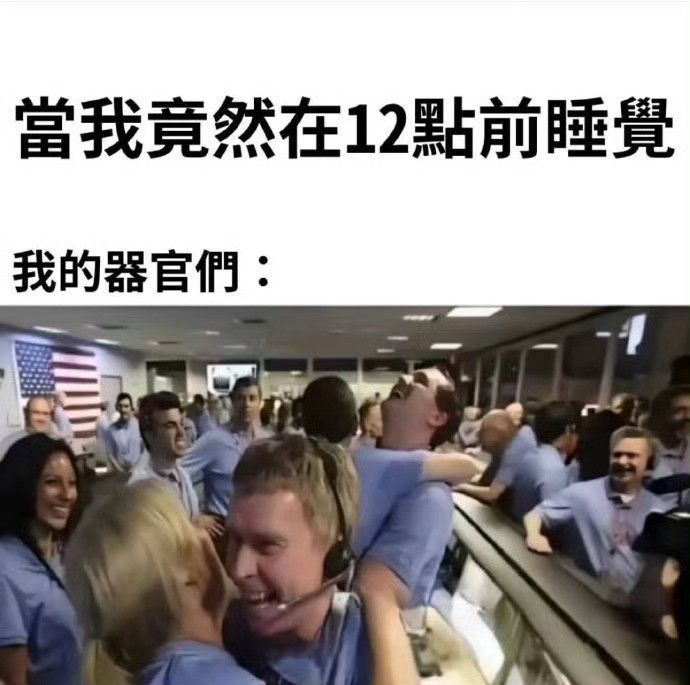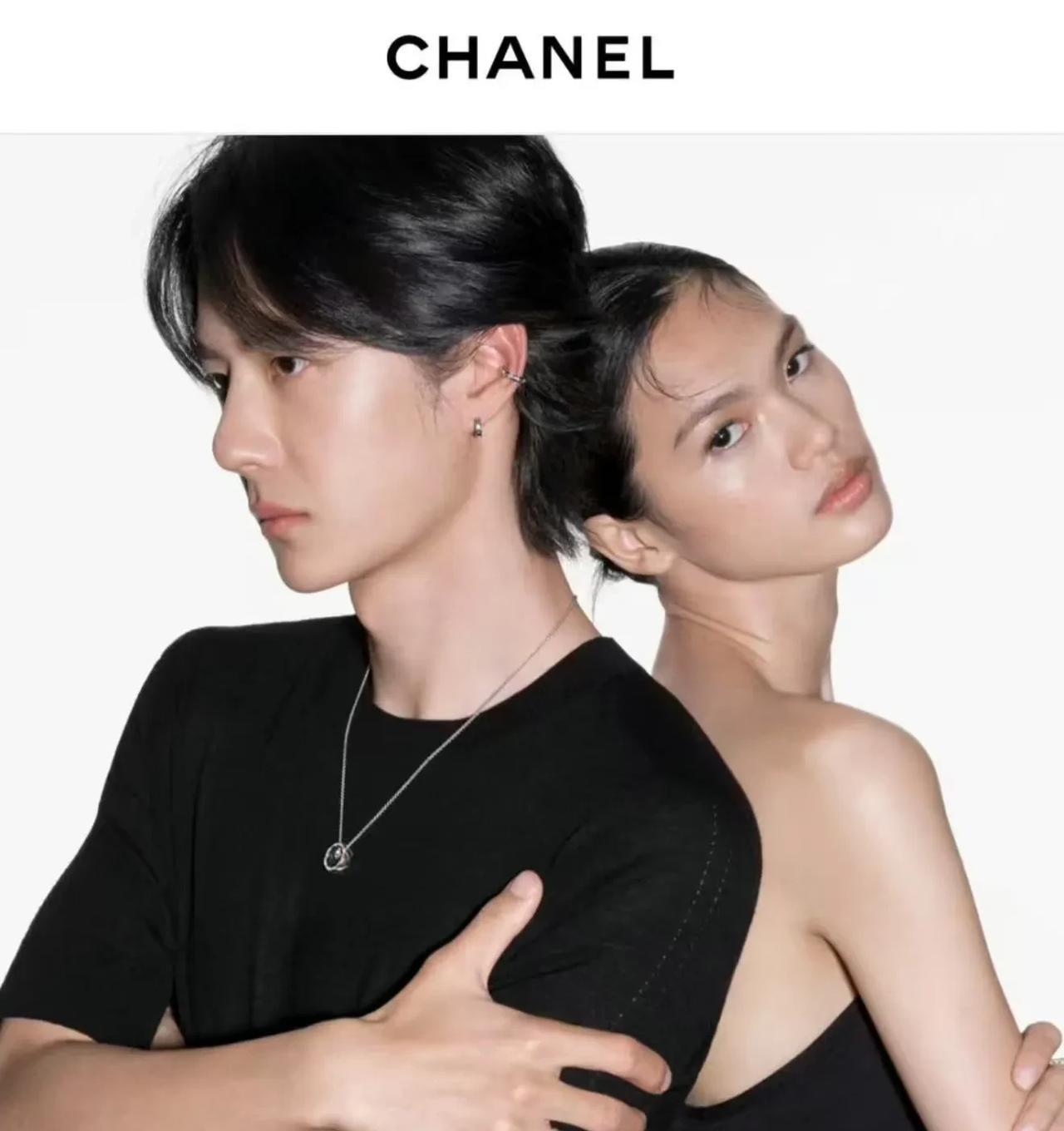1973年,知青刘朝旭被推荐上大学,临行前特意去找队长道别。未曾想,在他家窗前,听到队长低沉的声音:“朝旭要走了,去给他凑点路费吧!”队长媳妇无奈叹道:“你上次卖了羊皮袄才勉强给知青们置办了锅,现在让我去哪儿张罗啊!”
那年的冬天特别冷,陕北黄土高原上的风像刀子一样刮人脸,刘朝旭蹲在知青点的土炕上,借着煤油灯的光亮反复读着那张大学录取通知书。
纸上的铅字印得不太清楚,可“北京大学”四个字看得他眼眶发热,这个从北京来的知青已经在李家沟插队三年,手上磨出的茧子比老乡们还厚。
郭队长家就在知青点后面,土坯房低矮得进门要低头,那天清晨刘朝旭去告别,刚走到糊着旧报纸的窗户底下,就听见里面传出拉风箱似的咳嗽声。
郭队长肺不好,去年冬天带人修梯田时在雪地里泡久了落下的病根,屋里传来窸窸窣窣的动静,队长媳妇压着嗓子说:“箱底还有半匹土布,要不给娃缝件褂子?”
郭队长闷声应着:“再包二十个鸡蛋,城里学生食堂油水少。”
这些话像烧红的烙铁烫在刘朝旭心上,他记得刚来那年水土不服,是郭队长连夜赶着驴车送他去县医院。
队里分粮时,总把最稠的糊糊舀给他这个“京城来的读书娃”,现在要走了,怎么能再让这对老夫妻为难?
他故意把脚步踩得啪啪响,掀开打着补丁的门帘就喊:“队长,我娘寄来新棉鞋啦!”
炕桌上的煤油灯芯突然爆了个灯花,郭队长攥着烟袋锅的手顿了顿,抬头时皱纹里还夹着没散尽的愁容。
刘朝旭把挎包里的旧军大衣抖开,故意说得眉飞色舞:“您看这领子多厚实,我爹当年在朝鲜战场穿的,北京家里非要给我买新的,这旧的扔了多可惜。”
其实哪有什么新大衣,他藏在被窝里打补丁的袜子还有三双。
队部院里的老槐树掉光了叶子,树杈上挂着霜,刘朝旭走的那天,全村人挤在晒谷场送行。
郭队长把个蓝布包袱塞进他怀里,硬得像块石板,后来在火车上打开,是五斤晒得梆硬的柿饼和一双千层底布鞋,鞋垫里缝着皱巴巴的十块钱,票面上还沾着炕灰。
这事过去五十年,北大教授刘朝旭的书柜最上层始终摆着那双没舍得穿的布鞋,去年他回李家沟给郭队长扫墓,发现当年知青点的土墙早塌了,新盖的村委会墙上挂着“乡村振兴示范村”的铜牌。
村里九十岁的王婆子拽着他念叨:“郭老汉临走在炕席底下还压着你那张穿学士服的照片哩。”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很难想象,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一筐鸡蛋能换半本《新华字典》,一件羊皮袄抵得上全队半年的工分。
但正是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温暖,像黄土高原上的星星草,在裂缝里扎根,在干旱中开花。
当年全国270万知青里,有30万人通过推荐上了大学,他们背后都有无数个“郭队长”在默默托举。
站在郭队长长满青蒿的坟前,刘朝旭忽然明白,所谓“滴水之恩”,从来不是简单的投桃报李。
那些在困顿中依然选择善良的普通人,他们给出的不只是一碗糊糊、一双布鞋,而是一个民族在最艰难岁月里依然保持的尊严与温度。
这种温度穿越半个世纪,至今仍在黄土高坡的沟壑间静静流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