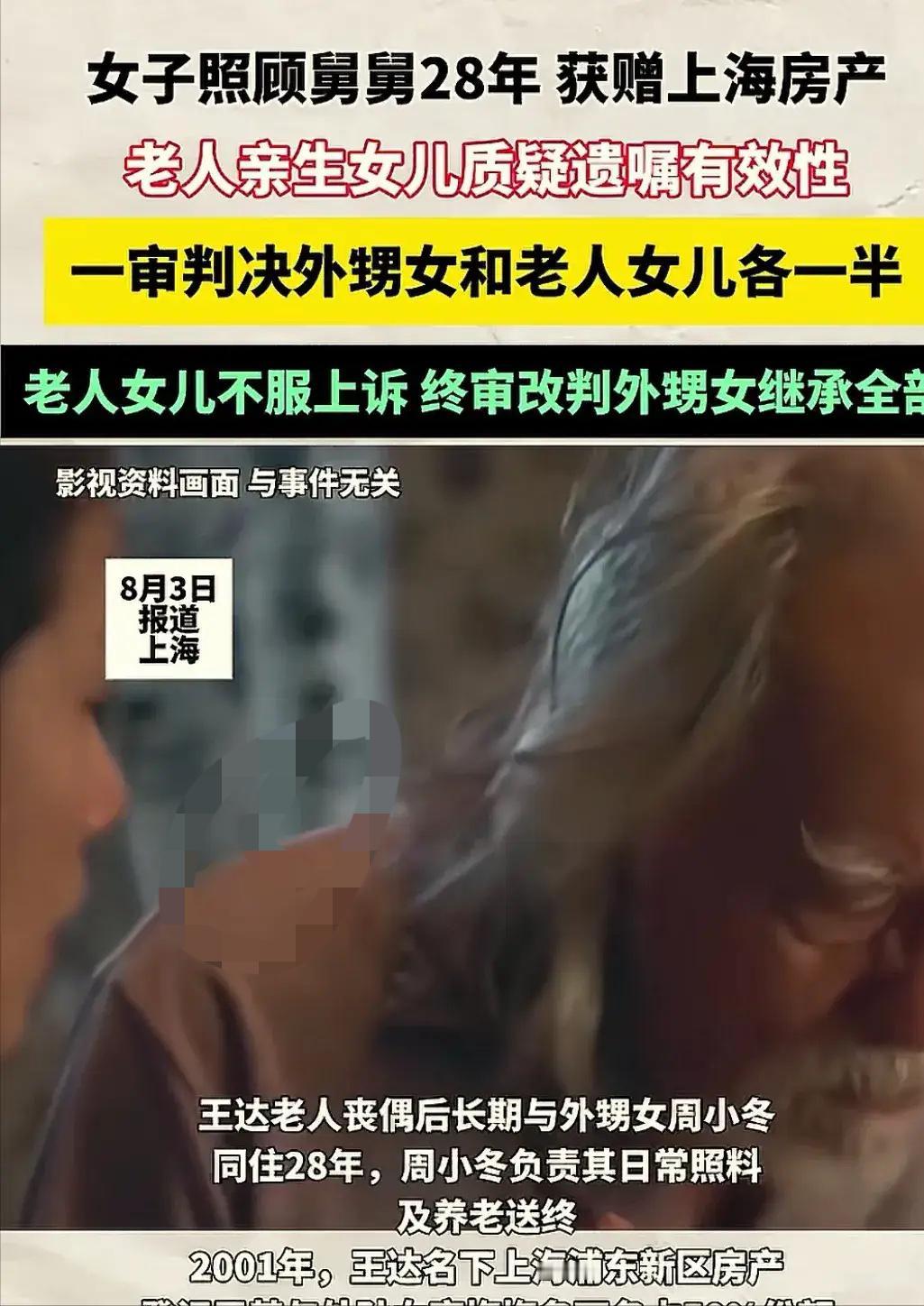“太寒心了!”上海一位老人去世后,远在国外的女儿火速赶回,直奔法院要求继承全部房产,可她不知道,老人早已将房子留给了照顾自己28年的外甥女,女儿一怒之下将表姐告上法院,法院最后这样判了! 上海老宅风波:28年陪伴与血缘的法庭较量 "这房子是我的!我是他亲闺女!"上海徐汇区法院的调解室里,王琳把护照拍在桌上,红色封皮上的金色国徽晃得人眼晕。她刚从纽约飞回来,时差还没倒过来,就为父亲留下的老洋房跟表姐周小冬较上了劲。 一、老洋房里的28年 1995年的夏天,周小冬拖着蛇皮袋站在上海弄堂口,舅舅王达穿着的确良衬衫在弄堂口等她。"小冬,跟舅舅回家。"老人往她手里塞了根绿豆冰棒,冰水滴在水泥地上,洇出一小片深色。 那时王琳刚出国,王达的老伴走了三年,家里冷清得能听见钟摆响。小冬住进来的第一个月,就把积灰的阳台收拾出来,摆上从老家带来的茉莉花。每天清晨五点,她踩着木楼梯下楼的声音,成了王达新的生物钟。 "舅舅,今天熬了小米粥,您胃不好得多喝点。" "小冬啊,这衬衫袖口帮我缝两针?" "舅舅您慢点,这台阶滑。" 日子像弄堂里的阳光,慢悠悠地淌。王达有高血压,小冬手机里存着社区医生的电话,药盒上贴着吃的时间;冬天老人腿冷,她每晚睡前都用热水袋焐热被窝;就连王琳每年寄来的保健品,都是小冬按剂量分好,装在小药盒里。 2010年王达突发心梗,在医院躺了半个月。小冬请了长假守着,头发熬得枯黄。王达清醒后拉着她的手,浑浊的眼睛里有泪:"小冬,这房子,将来给你。"小冬当时红着眼眶笑:"舅舅您好好活着,说这些干啥。" 第二年春天,王达让律师来了家里,立遗嘱的时候特意录像。老人坐在沙发上,背挺得笔直:"我自愿将名下房产赠与外甥女周小冬,感念其二十八年照料之恩。"镜头里,小冬正在厨房炖排骨汤,砂锅咕嘟的声音隐约能听见。 二、千里奔丧,撕破脸皮 王琳是接到律师电话才回来的。飞机落地那天上海下着雨,她穿着香奈儿套装走进老洋房,红木家具上蒙着白布,空气里有香烛的味道。 "表姐,我爸的房子呢?"王琳摘下墨镜,语气带着理所当然。 周小冬正在收拾老人的遗物,手里拿着王达常穿的羊毛衫:"舅舅立了遗嘱,房子给我。" "遗嘱?他老糊涂了吧!"王琳提高了嗓门,"我是他亲闺女,你算什么东西?" 小冬把遗嘱复印件递过去,王琳扫了两眼就撕了:"肯定是你骗他签的!我每年给他寄钱,哪回少于一万?你不就是图这套房!" 争吵声引来了邻居。张阿姨在弄堂里住了一辈子,拄着拐杖过来说理:"小王啊,你爸上次摔断腿,是小冬背着去的医院;去年冬天大雪,她凌晨三点扫雪怕你爸出门滑倒。你呢?你爸走的时候,喊的还是小冬的名字。" 王琳不听,第二天就把周小冬告上了法庭。开庭那天,她请的律师列出一堆汇款凭证:"法官请看,我当事人多年来持续履行赡养义务,作为法定继承人,理应获得全部房产。" 小冬没请律师,她抱着一个纸箱,里面是二十八年的记忆:有王达写的感谢信,有她记的护理日记,有每年春节两人的合照,还有那段立遗嘱时的录像。 "法官,"小冬的声音有点抖,却很清楚,"我不是图房子。但这二十八年,我跟舅舅不是亲人,胜似亲人。"她拿出一张泛黄的纸,是2003年王达写的:"今日小冬为我洗衣做饭,陪我看病,亲女远在天边,幸有小冬在侧,晚年不孤。" 三、法庭判决,人心自明 调解那天,王琳依然咄咄逼人:"她就是个保姆!我爸给她工资了吗?没有的话,这房子就该抵工钱,多出来的还得给我!" 周小冬忽然哭了,不是嚎啕大哭,是那种憋了很久的哽咽:"我照顾舅舅,不是为了钱。他走的前一天,拉着我的手说'小冬啊,谢谢你让我没当孤老头子'。这话,比房子金贵。" 法官最后宣判时,阳光透过法庭的窗户照进来。"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三十三条,公民可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与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本案中,被继承人遗嘱真实有效,且有充分证据证明受赠人尽了主要赡养义务。判决如下:系争房产归周小冬所有。" 王琳听完就炸了,指着法官骂"不公",最后被法警请了出去。小冬走出法院时,张阿姨带着几个邻居在门口等她,手里拎着刚出锅的生煎包。 "小冬,别往心里去。" "这世道,还是讲道理的。" 小冬回老洋房的那天,把王琳撕坏的遗嘱碎片捡起来,用胶带一点点粘好。夕阳照在阳台上,那盆茉莉花还开着,香气漫过木楼梯,像无数个清晨,她端着粥下楼时闻到的那样。 这栋房子最后没卖,小冬依旧住在里面。有时她会坐在王达常坐的藤椅上,想起老人说过的话:"人活一辈子,图的不是房子多大,是身边有个人,知冷知热。" 弄堂里的老人们说,这判决公道。毕竟,有些东西,比血缘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