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高炽登基第七日,朱高炽召见三法司官员,指着方孝孺案卷宗问大臣:“诛十族之说,可是先帝本意?” 乾清宫的铜鹤香炉里飘着龙涎香,烟缕在晨光里打了个旋,正落在案头那叠泛黄的卷宗上。三法司的三位大臣齐刷刷跪下,为首的刑部尚书金纯额头快贴到金砖上,声音发紧:“回陛下,洪武三十五年卷宗记载,方孝孺拒草即位诏,先帝怒命……夷十族。” “怒命?”朱高炽拿起卷宗最上面的纸,手指按在“十族”两个字上,指节泛白。他刚熬过二十多年的监国生涯,腰上的赘肉还没来得及适应龙袍的束带,说话却带着不容置疑的沉缓,“朕读《国史》,洪武年间定刑律,最酷者不过夷三族。先帝戎马半生,难道不知十族意味着什么?” 金纯喉结滚了滚,没敢接话。旁边的大理寺卿虞谦偷瞄了眼御座上的皇帝,这人昨天还在批奏折时念叨“山东赈灾要快”,今天却揪着三十多年前的旧案不放。永乐大帝朱棣的牌位还在太庙香案上摆着,新君这话,像是在问卷宗,又像是在问满堂的人。 “陛下,”都察院左都御史刘观突然开口,声音带着点豁出去的沙哑,“当日方孝孺在奉天殿骂先帝‘燕贼篡位’,还掷了御笔。翰林院编修的笔录里写着,先帝当时把朱笔往地上一摔,说‘你不怕灭九族?’方孝孺说‘便十族奈我何’——” “所以就真的诛了十族?”朱高炽把卷宗往案上一放,纸页翻动的声音在大殿里格外清响。他想起小时候跟着爷爷朱元璋读书,老爷子拿着《大明律》教他“法者,治之具也,非刑之具”。那时父亲朱棣还在北平当燕王,会摸着他的头说“阿炽要记住,法外有情,方是仁君”。 这话他记了四十年,记到看着弟弟朱高煦在父亲面前舞刀弄枪,自己却在文华殿里核赈灾粮册;记到父亲五次北征,他守着南京城处理堆积如山的奏折;记到上个月父亲驾崩,他在龙椅上坐了七天,夜夜梦见奉天殿的地砖缝里渗着血。 “传朕旨意,”朱高炽忽然站起身,龙袍的下摆扫过案几,带起一阵风,“方孝孺一案,除本人外,其余被株连者凡存活者,一律赦免。查抄的家产还给他们,愿意回原籍的给盘缠,想留在京城的入匠户、农户,不准再以‘奸党家属’相待。” 金纯猛地抬头,眼里满是惊惶:“陛下!先帝遗诏……” “先帝遗诏里说‘内外百司,务崇宽政’,”朱高炽打断他,走到殿中那面巨大的《大明疆域图》前,手指点在浙江宁海的位置,那是方孝孺的老家,“三十多年了,宁海的方氏族人,连孩子都知道自己是‘奸党之后’,走路都得低着头。先帝在世时,需要威服天下,朕现在要做的,是让天下人知道,大明朝的律法,不是用来泄愤的。” 虞谦磕了个头,声音里带了点颤:“陛下仁心,但……方孝孺毕竟是‘逆臣’,这样做,会不会让天下人觉得先帝……” “先帝是朕的父亲,更是开创永乐盛世的君主。”朱高炽转过身,阳光从窗棂照进来,在他脸上投下明暗交错的光影,“他当年或许有不得已的苦衷,但朕是新君,要走的路,和他不一样。洪武爷定的规矩里,有‘疑罪从无’,有‘老幼废疾减免’,这些才是我大明的根本。” 三法司的官员退下时,脚步都有些发飘。他们没注意到,御座旁的小几上,放着一本被翻得卷了角的《孟子》,其中“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那页,用朱砂笔圈了又圈。 三日后,赦免方孝孺族人的旨意传到浙江。宁海县城里,一个姓方的老妇人正给孙子缝补丁,听到官差宣读圣旨,手里的针线“啪嗒”掉在地上。她想起三十多年前那个血雨腥风的早晨,丈夫被铁链锁走时,回头喊的最后一句话是“记住,咱们没做错事”。如今圣旨里说“既往不咎”,她摸着孙子的头,忽然笑出了眼泪。 朝堂上却炸开了锅。英国公张辅拿着奏折冲进文华殿,跪在地上红着眼说:“陛下!臣父张玉当年为救先帝,战死于东昌,方孝孺的党羽至今还在骂我张家是‘燕贼爪牙’!您这样做,对得起先帝,对得起战死的功臣吗?” 朱高炽让人给张辅搬了个锦凳,自己也坐下,慢悠悠地说:“英国公,你父亲是功臣,朕年年派人去东昌扫墓。可方孝孺的族人里,有七岁的孩子,有八十岁的老人,他们没拿过刀,没骂过先帝,凭什么要背着‘奸党’的名声过一辈子?”他拿起桌上的一个苹果,用刀切成两半,“这天下就像这苹果,先帝削掉了烂掉的地方,朕要做的,是让好的地方长得更结实。” 张辅张了张嘴,最终没再说什么。他想起永乐大帝晚年,常对着北方的地图叹气,说“阿炽仁厚,将来必能安天下”。那时他不懂,现在看着御座上那个胖乎乎的皇帝,忽然有点明白了。 深秋时节,朱高炽下旨重修方孝孺故居,只保留一间正房,不许立碑,不许题字。落成那天,他微服去了趟宁海,站在院子里看了看天,转身对随从说:“历史这东西,有时候像块石头,压得人喘不过气。朕挪不动整块石头,能搬走一点是一点。” 那年冬天,朱高炽驾崩,在位只有十个月。但南京城的百姓记得,这位胖皇帝在位时,监狱里的犯人少了,赈灾的粮食多了,连街面上讨饭的孩子,都能领到官府发的棉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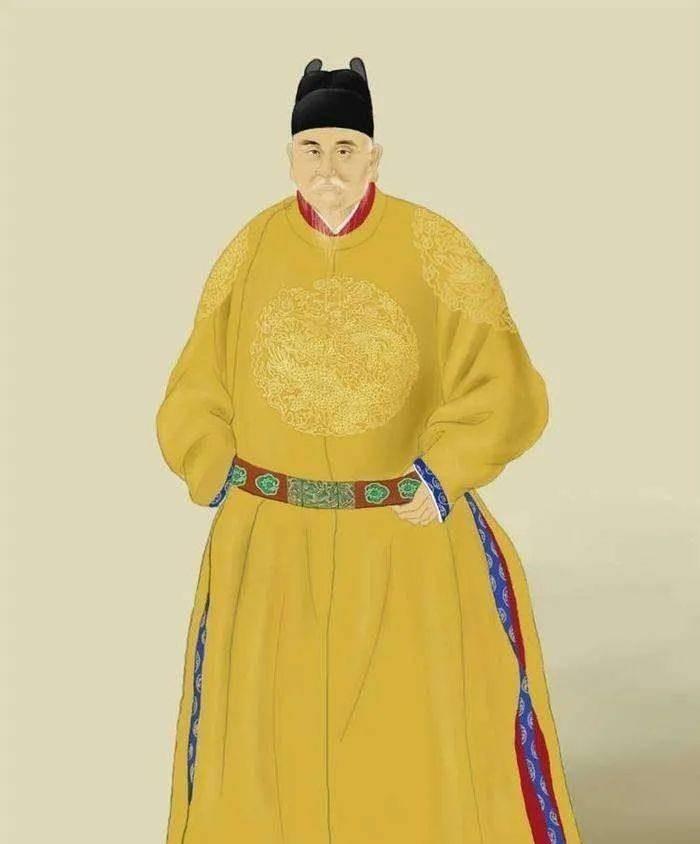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