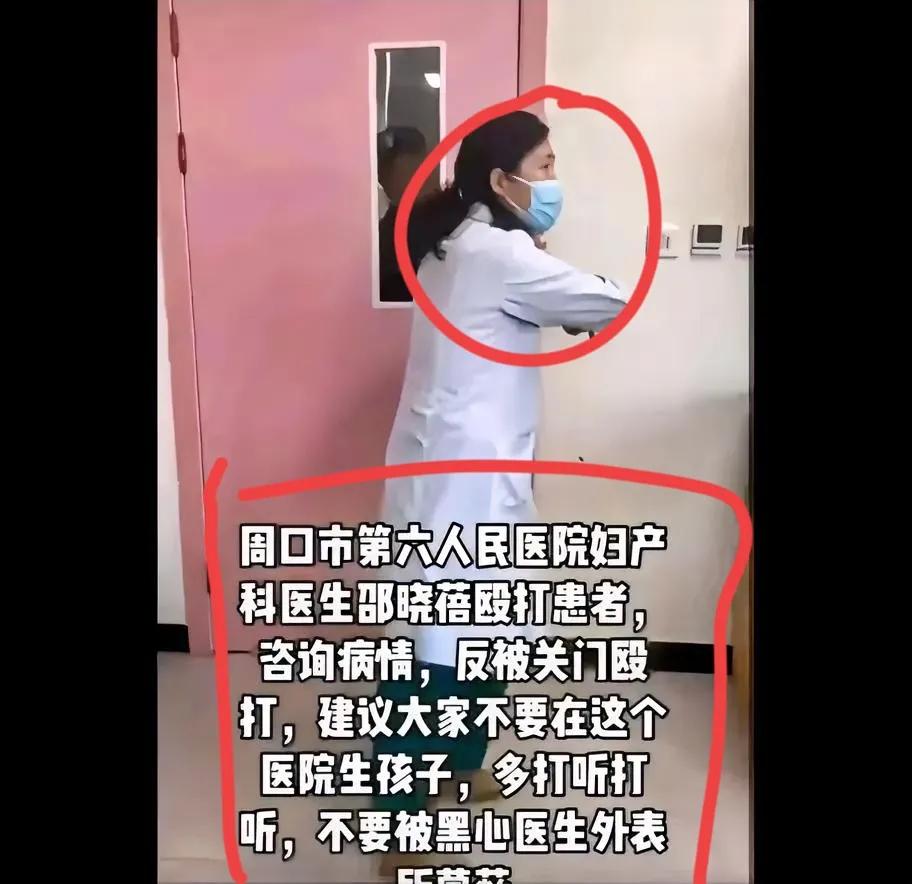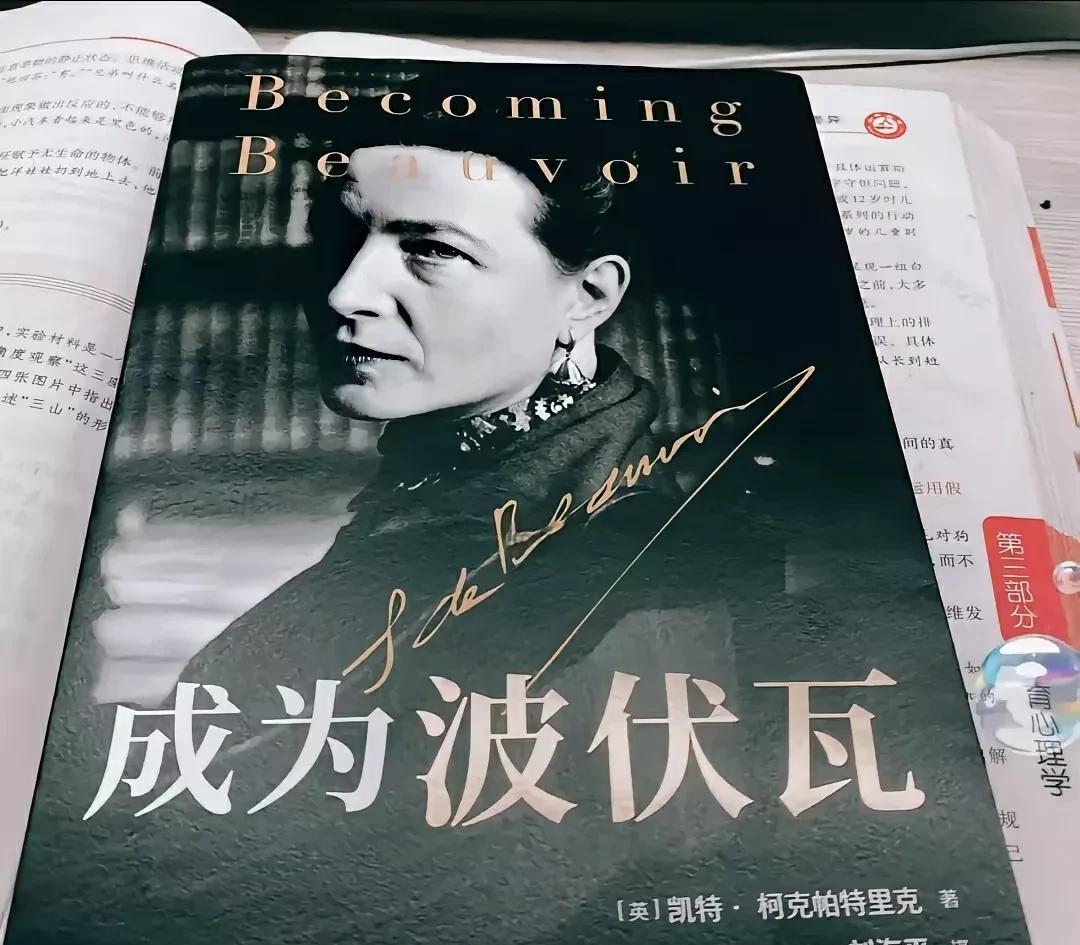在中国服饰发展史上,最早原始社会人们对于美的追求较为简单,过着“食草木之实,衣禽兽之皮,饮其血,茹其毛,未有丝麻,衣其羽皮”的原始生活。 兽皮、未经鞣制加工的皮毛等被用于遮羞蔽体和保暖御寒,此后相继出现了棉麻丝毛类纤维编织而成的纺织品,纺织品类文物种类逐渐呈现多样化。 随着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文化间的交流,尤以中国丝绸作为国与国之间主要流通物,等价交换和贸易往来的方式,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地区间的经济发展,这在织物图案纹样上也有较为突出的表征。 就功能性而言,新疆黑山岭遗址出土的纺织品可以体现古代先民的审美能力,特殊的图案纹样彰显着鲜明地域化特色,采矿先民也更加注重织物的实用性,有些图案纹样也从夸张的抽象派转化为写实风格。 新疆黑山岭遗址出土纺织品多是素面,其图案纹样主要是几何纹样和动物纹样两类。 从审美角度来看,新疆出土过很多与萨满教相关的遗存,其中就有鹿这一动物形象的发现。 在石板上雕刻飞鹿形象,鹿石主要见于东天山所覆盖的阿尔泰地区,发现年代聚焦于青铜时代晚期到早期铁器时代,多伫立在祭祀性石结构建筑附近。 鹿的动物形象不止在岩画、陶器上出现,也常存在于纺织品上,洋海墓地就有带鹿纹的法衣残片出土。 这种呈飞翔状的鹿纹在黑山岭纺织品残片上出现,线条流畅,排列成一行,鹿角用夸张手法表现,用鸟的喙首、鸟的细腿,鹿的身体和花角组成的鸟鹿合体动物,体现了当地居民的宗教信仰,与萨满教有一定的关联性。 萨满是天地间与人类沟通的使者,而鹿善于奔跑,鸟能够翱翔,这与信使的接力相关,二者结合表现出万物有灵的宗教意识。 飞鹿的动物纹样有可能与当时采矿先民的图腾崇拜有关,也可以看出纺织品残片上对鹿这一动物的神化是人类与自然共生时对自然的敬畏。 此外,新疆黑山岭遗址出土纺织品残片上鹿纹的鹿角与巴泽雷克文化的格里芬形象相类似,早在早期铁器时代就已经存在着迁徙和融合现象。 动物纹装饰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采矿先民与巴泽雷克人群间可能存在着共通的思想、习俗或者某种观念,反映了东西方文化间的交流与传播。 云雷纹是西周时期青铜器上常见的几何纹样,在玉器、陶器、铜镜、漆器、建筑物中也常作为装饰纹样使用。 新疆黑山岭遗址出土纺织品文物上的几何纹样为雷纹,呈方折的线性回旋线条,正反形二方连续构图,布局规整、排列有序,讲究对称美与韵律感。 这一纹样体现了当时采矿先民的宗教意识,象征着权力地位的等级划分和人文主义思想。 表达对云、雷等自然载体的崇拜意识与采矿先民从事采矿活动时对气候环境条件的需求所契合,把握审美性的同时注重织物的实用性。 西域居民衣服无纽扣时,多用带子捆绑于腰间,防止衣襟不散开,起到绑扎固定作用,使得古代先民穿着更为得体。 根据新疆的考古发掘资料,洛浦县山普拉墓地出土的腰带用毛线编织为主,鲜有皮带,宽窄度不一,宽度最宽可达10㎝,最窄1.7㎝,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 反映了于阗国人在当时社会发展背景下的束带习俗和区域化。腰带的长度具有一定的参照性,它是由人的体型变化决定的。 而新疆黑山岭遗址出土的质地较为粗糙,用一种颜色的粗毛线编织而成,没有多种色彩变化形成的花纹或图案,有一定的韧性。 毛绳两端打结共三个,可能是用于悬挂工具等采矿活动时为防止带子断裂,进行多次加固,使其更结实耐用。 这一双股绞转编织的原色毛绳主要是采矿先民在矿区为了劳作方便而捆绑于腰部固定衣服,并且达到了明显的装饰效果,具有很强实用性。 近年来新疆地区出土的纺织品虽然棉麻丝毛类均有,但主要以毛纺织品为主,纺织品作为新疆古代居民日常生活中必需品,毛纤维是服饰缝制加工时所使用的主要纤维原料。 如在小河墓地曾考古发掘出土毛绳、毡帽和腰衣,毛绳主要用于草编篓的提手处或在帽外缠绕一周,达到装饰效果和承载重物。 而黑山岭矿区也出土大量芨芨草和籽种,所研究样品中间夹杂草屑,这一现象与洋海墓地草编篓制作材料也相互印证,可见当时矿区对芨芨草的利用率较为频繁,有可能用来制作草编篓之类的物品,用于储物或运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