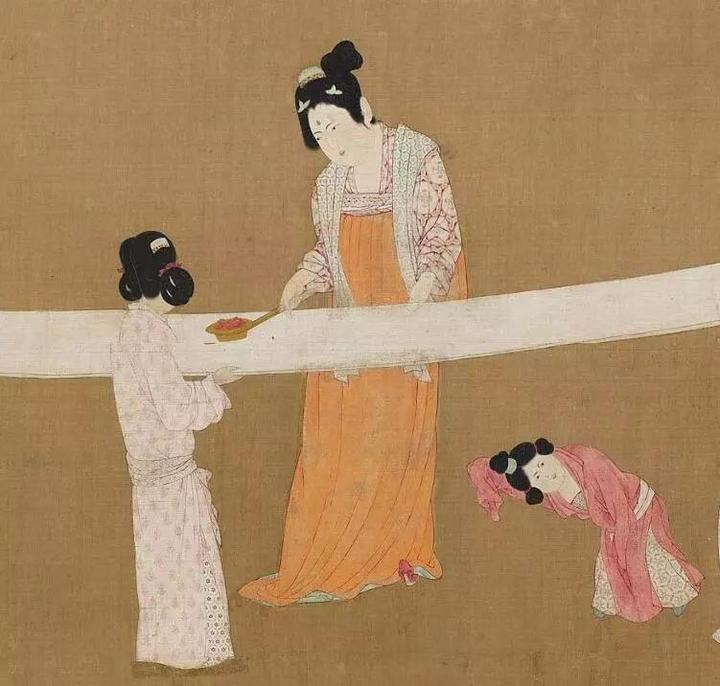纤维原料选择与编织工艺,是西北地区纺织考古史上常见的原材料,古代先民通过加工动物毛纤维,获得多种类型的毛织物,诸如毛绳、毛毡、毛编带、毛毯、毛绦带等。 黑山岭遗址周邻地域以往的考古发现中曾出土多类毛织品,如艾斯霞克尔墓地出土大量毛织衣物,如毛布长裤、长袍、编织带、裹巾、帽和毡袜。 毛编带则多用于串珠饰,佩戴在手腕或臂处,兼具实用性和审美性。因此,黑山岭出土大量的各式毛织物并不偶然,而是当地气候条件、生业模式和生活习俗共同作用的结果。 新疆黑山岭遗址出土纺织品的编织工艺包括纱线加捻方式、缝制工艺、组织结构、经纬密度、纺织工具等方面。 在纺织加工工具方面,黑山岭遗址区发现骨针、纺轮、羊毛刷、木质绕线轴等纺织工具,表明在生产类遗址区的矿业人群在从事矿业生产的同时,也进行纺织加工活动。 此外,黑山岭遗址周邻地区也曾有纺织工具发现,如焉不拉克墓地圆形陶质、骨质纺轮、骨针等。 相比于其它墓地,黑山岭遗址的纺织工具较为简单,这可能主要是因为该遗址是生产类遗址,而不是定居型生活遗址,其纺织工具的存在意义更倾向于满足日常基本生活和生产需求。 从纱线的加捻方式来看,黑山岭遗址出土纺织品包括无捻、S捻和Z捻三种。 大多数纺织品采用Z向加捻,占总数的一半以上,而采用S捻的织物仅占10%左右,这表明矿业人群存在两种不同的加捻习惯,大多数习惯使用Z向加捻,少数人习惯使用S向加捻织物。 另有部分纺织品的纱线加捻方式较弱甚至难以辨识,加捻强度降低,可能是矿业人群劳作中的不断磨损,使得捻向变弱。 新疆黑山岭遗址出土纺织品的捻向以Z向为主,经纬线同捻向和经线或纬线Z向的织物,占比78%。同一织物,存在两种加捻方式可以使得织物结构的疏密程度产生差别。 汉以前用纺轮加工织物的较多,汉代出现手摇纺车后,古代先民更习惯用右手加工,左手加工者所占比例逐渐减少。 从黑山岭遗址出土纺织品的纱线加捻方式可以发现矿业人群更习惯于用右手,且经纬线异向加捻的配置方式加强了织物的牢固强度。 使得织物具有更好的耐磨性,更有利于矿业人群的繁重的采矿劳作,从而满足采矿人群的生产需求。 此外,黑山岭纺织品有单层双层之分,经纬线粗细不等,该遗址出土的纺织品在矿区具有一定的选择性,纺织品的疏密程度和厚薄变化。 表现了生产生活类遗址区特殊的气候条件和采矿过程的劳动强度,表明矿业人群的穿着既要满足采矿生产活动,更好地适应昼夜温差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采矿活动的季节性。 从编织结构和缝制工艺来看,新疆黑山岭遗址出土纺织品的编织结构紧密,以一上一下的平纹组织结构为主,也存在1/2、1/4编织而成的组织结构。 有些织物边缘处以绞编技术加工,提高其耐牢度,为更好地满足矿业人群在采矿过程中的穿着需求。 动物纹样采用缂织技法编织而成,使得纹饰正面具有立体感。此外,双层纺织品多采用锁针、平针的缝制方式,缝补矿业人群在采矿过程中劳作磨损的织物。 一方面,新疆黑山岭遗址出土纺织品在原材料选择和编织工艺方面,与周边多处墓葬出土纺织品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另一方面,黑山岭遗址出土纺织品的编织技法多样化,具有高度复杂性,这虽与较为单一的纺织工具相矛盾。 但可以反映出黑山岭遗址纺织品具有双重特性,既能够体现矿业人群的生产生活物资的外部补充,也存在为了满足遗址内部的需求,而进行的现场加工或修补活动。 包括斜编、结构单一的平行编、组合编 三种编织方法,斜编细分为交叉、绞编、交编、纠编。 这一研究表明早在西周时期新 疆毛纺织品就已经有一套成熟的编织工艺。汉晋时期西域已出现绞版式织,它们正是在西亚早期文明、中亚贵霜及草原文化圈交流传播的影响下,从本土元素向希腊化风格过渡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