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朱梅馥为傅雷准备好温水,等他服下剧毒药物后,她又帮傅雷摆正仪容,然后撕下床单做成绳索,挂在卧室的钢窗上。怕打扰别人,她在凳子下垫了棉胎,最后深情望一眼丈夫,也随他去了另外一个世界。
那年秋天的北京城,树叶还没完全变黄,街上已经透出凉飕飕的冷意,傅雷家院子里的海棠花早谢了,只剩下光秃秃的枝杈在风里摇晃。
这对过了几十年的一双夫妻,正在经历人生最后的时刻。
要说这俩人的缘分,那得从他们穿开裆裤的时候说起,傅雷和朱梅馥是远房表亲,打小就在一个院里玩耍。
朱家这姑娘七岁就会弹钢琴,手指头在琴键上跳舞似的,傅家小子就爱趴在琴凳旁边听,两家大人看他们要好,在傅雷十四岁那年给定了娃娃亲。
后来傅雷去了法国念书,巴黎那地方花花世界,小伙子难免迷了眼,他喜欢上当地一个叫玛德琳的姑娘,这法国妞儿长得漂亮又有见识,把傅雷迷得五迷三道。
傅雷当时脑子一热,写了封信回家要退婚,信都写好了,临寄出去又后悔,托朋友刘海栗先保管着,结果玛德琳压根没想嫁人,傅雷这才醒过味来,还是家里那个表妹最贴心。
1932年腊月里,两人在上海成了亲,新婚头几年确实甜蜜,俩人你弹琴我读书,院子里种满月季花。
可惜好景不长,头胎孩子没保住,傅雷老娘又跟着走了,接连遭难,傅雷整天闷在书房里叹气,朱梅馥就变着法哄他高兴,今天炖莲子羹,明天摆弄他喜欢的君子兰。
要说这朱梅馥对丈夫真是没得挑,傅雷脾气倔得像头驴,翻译书稿时稍不顺心就摔东西,有回把墨水瓶砸墙上,墨水点子溅得到处都是,朱梅馥不声不响收拾干净,连句埋怨都没有。
更难得的是,傅雷后来在外头有了相好的,朱梅馥不但没闹,反倒把那个姑娘请到家里做客、,街坊邻居都说她傻,她却说只要老傅心里痛快,怎么着都行。
日子就这么磕磕绊绊过到了1966年,外头闹得越来越凶,傅雷这种搞学问的成了重点对象,红卫兵三天两头来抄家,书房里那些外国书被撕得七零八落,傅雷最宝贝的翻译手稿被扔在地上踩。
九月二号那天,两口子把家里存的安眠药都翻出来,可傅雷嫌药劲不够,非要找更狠的。
妻子这回没劝他,她烧了壶温水,看着丈夫喝下掺了毒药的米汤,等傅雷疼得在床上打滚,她拿热毛巾给他擦身子,把皱巴巴的中山装抚平。
丈夫咽气后,她马上撕开床单搓成绳子,并在自家的窗户框子上面系了个死扣,怕踢凳子的动静吵着邻居,特意在凳子底下垫了棉被。
后来收拾遗物的人发现,傅雷那些整整齐齐的翻译稿,全是朱梅馥一笔一画誊抄的,书桌抽屉里还压着当年没寄出去的退婚信,信纸都泛黄了。
街坊老邻居说起这事就抹眼泪:"多好的一对人啊,怎么就走到这步田地。"
要说朱梅馥这辈子,真应了她自己说过的话——两口子过日子就得互相担待,傅雷脾气再臭,她总念着他读书时的好;外头风雨再大,她始终守着这个家。
到最后关头,连死都想着不给别人添麻烦。这样的夫妻情分,现在怕是打着灯笼都难找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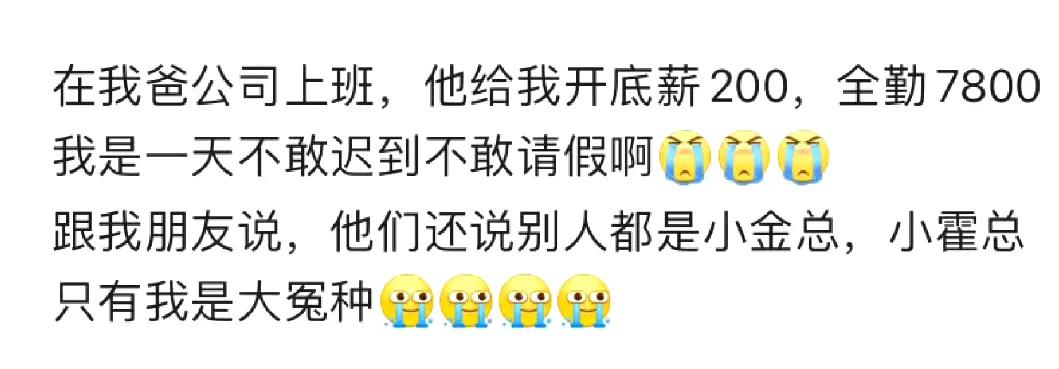

![早晚要笑死评论区。[裂开][裂开][裂开][裂开][裂开]](http://image.uczzd.cn/11544888580563898354.jpg?id=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