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张国立拉着王刚去找李保田说:“咱们三个组团拍戏,肯定火。”李保田却摆摆手:“戏都拍完了,我不玩了。” 1996年,《宰相刘罗锅》播出后火遍大江南北,观众们津津乐道,街头巷尾人人皆知“刘罗锅”。戏红了,投资方自然闻风而动,几大公司捧着钞票上门,希望拍续集。 张国王刚,几番合计后,决定拉上最关键的一环——李保田。 张国立亲自上门,语气热切:“咱们哥仨联手,这续集不火才怪!”王刚在一旁附和:“观众还没看够刘罗锅呢,这热度,不能错过!” 可李保田只是摇头,眼神淡然如水:“故事已经讲完了,续集不是创作,是重复,是骗观众的钱。我不演。” 一句话,像泼了盆冷水,浇灭了所有人的热情。 张国立有些急了:“观众喜欢我们,这叫顺势而为。” 李保田却淡淡回应:“观众喜欢我们演得真,不是喜欢我们凑热闹。” 这不是第一次,李保田因“固执”而显得“不合群”。 自他成名以来,广告商也没少找上门。某知名白酒品牌愿意开出七位数酬劳,请他喝一口酒、说几句吉祥话。药品广告更夸张,开口就是几千万,只要他说一句“灵”,他们就能铺天盖地打出去。 可李保田统统拒绝。他不喝酒,自然不能说“酒好”;他没有病,更不会为了代言胡吹疗效。他反问来人:“我不喝,你让我说好喝,我怎么说得出口?” 这样的执拗,实打实推掉了2000多万元的收入。在那个年代,2000万是什么概念?足以买下北京三四套别墅,换来十几年的无忧生活。 但李保田不为所动。他说:“一个演员,靠作品说话,不靠广告圈钱。若干年后,我希望人们记得我是演过好戏的人,不是哪个药的代言人。” 有剧本送上门,他一定要亲自读完,哪怕是五十集的长剧,也要逐字逐句看完;有角色找他出演,他不只看重片酬,而是看人物是否立得住,是否值得自己沉下心来演绎。 在拍摄《神医喜来乐》时,有场戏要他翻窗。他当时年近六十,却坚持不用替身,亲自完成。他说:“如果我都怕这个怕那个,观众凭什么相信我演的是‘神医’?” 他拍戏从不敷衍,从不抢戏,也从不迎合。他常说:“演员不能太聪明,太会算计的人演不了真戏。” 这份耿直,偶尔也会让人头疼。他不肯拍不合心意的戏,也不愿参与商业包装。某导演曾吐槽:“李保田太轴,有时一句台词要反复推敲十几遍,和他合作很累。” 在拍《葛老爷子》时,为了贴合角色形象,他硬是把自己的头发一遍遍漂染成银白色。那可是工业级染剂,不是现在这类温和产品。 结果,拍完戏他发现,头皮像被烧灼了一样,毛囊坏死,大把大把掉头发。别人劝他用假发、用化妆替代,他却摇头:“演员不能怕吃亏,怕疼还演啥戏?” 更让人敬佩的,是他74岁时还在拍《寻汉计》。那场戏需要他摔在水泥地上,剧组早早就安排好了替身。 可李保田坚持亲自上:“一看就能看出来是不是替身,观众又不傻。”导演劝他:“李老师,您年纪大了,真摔坏了我们担不起。” 他只说了句:“戏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镜头一响,他毫不犹豫地往地上一扑,重重地摔下去,那一声响,把全剧组都吓得直哆嗦。 拍完后,助理扶着他,他咬着牙说:“疼是真疼,但镜头也是真实。” 可真正让整个行业震动的,还是他跟《钦差大臣》的那场官司。 这部剧原本是30集,剧情紧凑,节奏合理。可制片方临时要求“注水”,加到33集,好多镜头拉长,甚至要李保田临时拍些没头没尾的过场戏来填时间。 他一看剧本,脸就拉下来了:“这是骗观众的时间,也是在糟蹋我们演员的劳动。” 他多次与剧组沟通无果,最后干脆一纸诉状,把制片方告上法庭。他在法庭上说的那句话,至今仍让人印象深刻:“老百姓连注水肉都不吃了,怎么还得忍着看注水剧?” 这句话,掷地有声,也让他赢得了胜诉。不仅拿到了违约赔偿,还为国产剧开了个先河:演员也有权利抵制“注水”。 但这场硬仗也带来了代价。事后,十几家影视公司联合抵制他,几乎没有人再敢找他演戏。他的戏路因此断了一大半,收入也大不如前。 可李保田一点不后悔。他说:“要是为了赚钱就,那我当初就接广告了。戏可以疯魔,但人得清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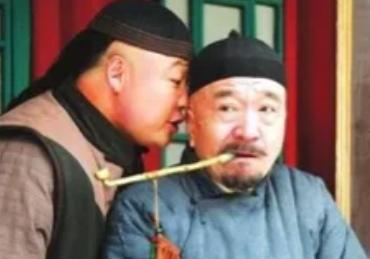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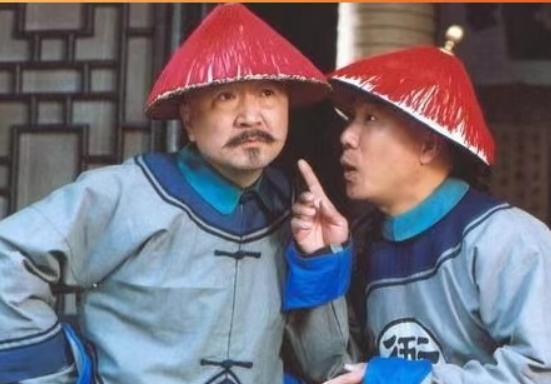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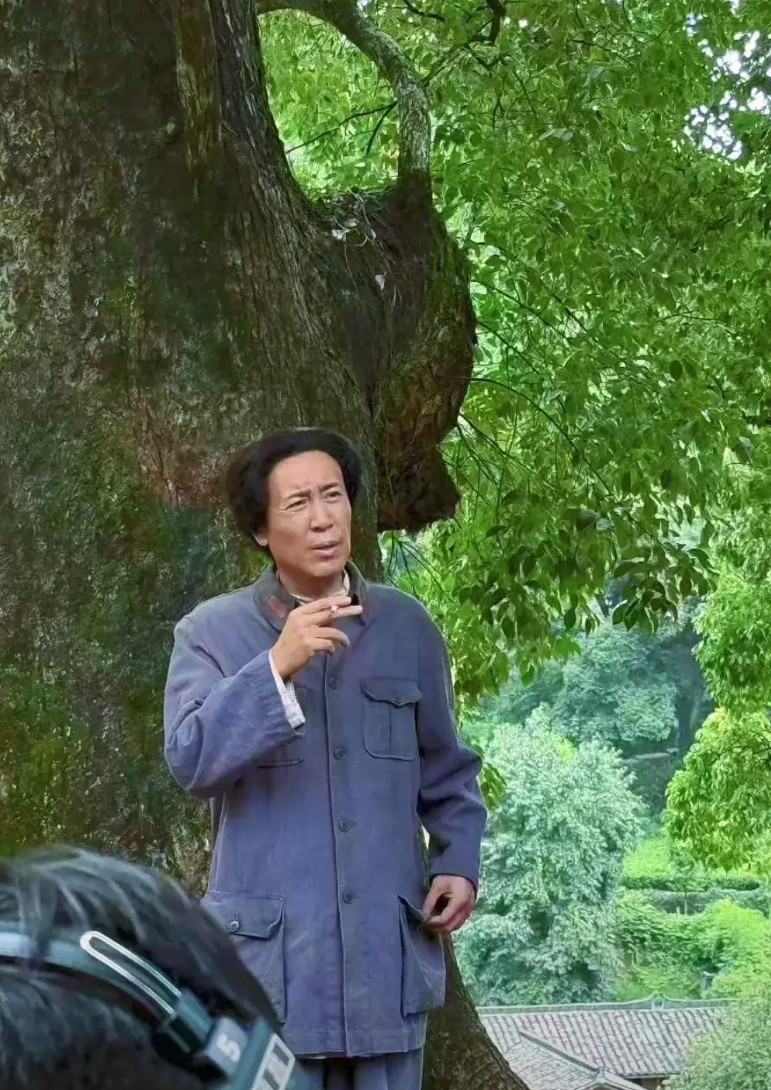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