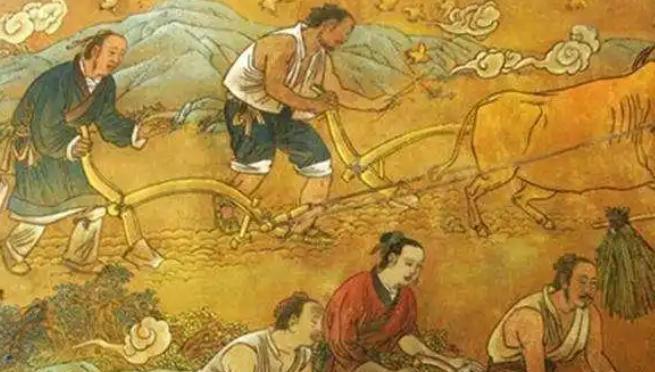1952年,弹道专家张述祖对陈赓说,有个弹道专家很稀缺,陈说,那就赶紧要过来呀,张却闪烁其辞,陈赓以为又要麻烦周总理,结果张来了一句:“恐怕天王老子也批不了他呀。” 当是刚从朝鲜战场硝烟里钻出来的陈赓,正为哈军工的筹建愁得满嘴燎泡。这天,弹道专家张述祖磨磨蹭蹭地找上门,手里攥着份发黄的档案,欲言又止的样子让陈赓心里犯嘀咕。 当时新中国的军工领域,像样的专家比金子还稀罕,尤其是玩火炮弹道的,全国能数得上来的也就那么几个,张述祖自己算一个,可他知道,还有个被埋没的人才,只是这人的身份实在太敏感。 张述祖吞吞吐吐地说,有个叫沈毅的留法专家,对火炮弹道的研究,在国内能排进前三。 陈赓一听眼睛亮了,拍着桌子让赶紧调过来,可张述祖的头摇得像拨浪鼓,支支吾吾半天,才说出沈毅这会儿正在监狱里蹲着呢,还是死缓。 这话像盆冷水浇在陈赓头上,他愣了愣,追问到底是啥大罪。 原来沈毅在民航总局当财务处长时,“三反”运动里查出他手脚不干净,贪污的数目在当时能买下半条街的房子,按律当斩,后来改判了死缓。 陈赓捏着烟卷在屋里转圈,烟蒂扔了一地。他太清楚缺人才的滋味了,哈军工刚起步,教弹道学的老师凑不齐一个班,学生们拿着苏联教材啃得头昏脑涨,因为很多专业术语根本没对应的中文词。 张述祖说得没错,沈毅确实是块好料,留法那几年专攻的就是大口径火炮的外弹道计算,这正是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急需的本事。 那会儿咱们的炮弹总打不准,不是射程差一截,就是落点偏得离谱,多少战士的命就这么没了。可把个死囚弄到军事学院来,这事儿听着就玄乎。 警卫处的人听说后直摆手,说这要是让敌特钻了空子,把弹道数据弄出去,可不是闹着玩的。政治部的同志也觉得不妥,刚打完“三反”,这时候把个贪污犯请到学院当老师,群众能答应? 陈赓却在会上拍了板:“人犯错该罚,但本事是国家的,放着不用才是真傻。”他让人去查沈毅的案子,发现这人虽贪财,却没给敌人办事,而且在抗战时还帮着兵工厂改过炮弹,有点民族骨气。 接下来的事更让人跌破眼镜,陈赓直接给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打了电话。 电话里他说得实在:“沈毅的罪该受罚,但他脑子里的学问,能顶一个炮兵团。要不这样,让他戴罪立功,在学院里搞教学,我们派专人盯着,出了岔子我陈赓担着。” 之后陈赓还分别请示了毛主席和周总理,最终改判沈毅“监外执行,由哈军工监管。” 沈毅被押到哈尔滨那天,戴着手铐脚镣,棉袄上全是污渍。陈赓亲自去火车站接,见了面就让人把镣铐卸了,指着身边的张述祖说:“从今天起,你跟张教授学怎么教书,把你那点本事全掏出来,教好了,算你立功。” 沈毅愣在那儿,半天说不出话,后来才知道,他在监狱里早做好了这辈子烂在牢里的打算,根本没想过还能碰弹道学的东西。 刚开始沈毅确实拘谨,住的翻译室里除了一张桌子就是铺着稻草的床,他每天抱着本《拉鲁斯词典》啃,把苏联教材里的公式一个个译成中文,旁边放着个小本子,记满了“初速”“射角”“空气阻力系数”这些新词的译法。 冬天屋里没暖气,他就把热水袋灌满热水裹在腿上,手冻得握不住笔,就在暖气片上烤烤接着写。 有回张述祖半夜查房,看见他屋里灯还亮着,推门进去发现沈毅趴在桌上睡着了,胳膊底下压着刚算好的弹道表,上面密密麻麻全是演算过程。 半年后,沈毅编的《155毫米加农炮外弹道计算手册》印出来了,学员们捧着这本带着油墨香的册子,总算不用对着俄文教材发呆了。 更神的是,按照手册里的公式调整炮位,学院试射的炮弹落点误差一下子缩小了一半还多。 有个从朝鲜回来的老兵参观完试射,拉着沈毅的手说:“要是早有这东西,上甘岭那会儿咱们能少牺牲多少人啊。” 可风言风语一直没断。有人写信到总政,说哈军工“藏污纳垢”。陈赓把信往桌上一拍:“沈毅在这儿教出的学生,将来是要去保家卫国的。他贪污的钱,咱们让他用炮弹的准头还回来,这账算得过来。” 沈毅心里有数,从不打听学院的机密,除了上课就是闷头搞计算,连食堂都很少去,总让人把饭打回屋里吃。 1955年评职称,张述祖提议给沈毅算“教员”待遇,又掀起一阵波澜。陈赓在党委会上说了句掏心窝子的话:“咱们共产党办事,得让人看到希望。沈毅犯了错,但他现在在赎罪,在为国家做事,这样的人,得给条出路。” 最后,沈毅成了哈军工唯一一个没有正式编制的“特约教员”,工资不多,但够他糊口。 沈毅后来在哈军工待了八年,参与编写了五本弹道学教材,培养出的学生里出了好几个工程院院士。1960年,他的刑期已满,学院给了他正式编制。 那天他拿着通知书,跑到陈赓的铜像前(当时陈赓已去世),恭恭敬敬地鞠了三个躬,眼泪掉在铜像的底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