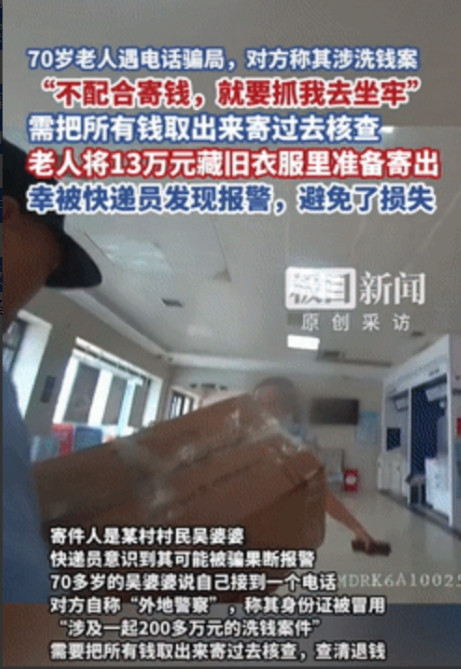1995年7月8日,为了抓捕乔立夫,兰州警方决定以8对1。 1995年的夏天,那时候,没“天网”,没健康码,更没无处不在的摄像头。一个高智商的亡命徒,往人海里一钻,就跟一滴水掉进了黄河,想捞出来,靠的是人,是经验,是胆识,还有那么一点点运气。 所以,当1995年7月8日,兰州警方为了抓一个人,从全局抽调了8名顶尖的刑警,去对付他一个,这事儿就透着一股子不寻常。这个人,就是乔立夫。 当年,乔立夫这三个字,在警界,尤其是南方,那可是挂了号的。他不是那种流里流气的混混,恰恰相反,他毕业于北京钢铁学院,正儿八经的大学生。在那个年代,大学生是什么概念?天之骄子。 可这位天之骄子,心没用在正道上。1993年6月16日,深圳。乔立夫伙同另一个狠人冯炳南,用极其残忍的手段,抢劫并杀害了两名香港商人,卷走了160多万港币。那可是1993年的160多万!足够在当时的深圳买下好几栋楼。 这案子一出,全国震动。公安部下了A级通缉令。但乔立夫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两年,整整两年,音讯全无。 他能藏,靠的就是他的脑子。反侦察能力极强,为人又冷静得可怕。据说他被捕后,审讯员都感慨,这人的心理素质,比我们一些老警察都强。他从不与家人联系,从不在一个地方久留,用着假身份,过着最普通的日子。这种人,最难抓。 两年后,线索终于浮现,指向了千里之外的兰州。 当时的兰州警方接到协查通报,压力巨大。一个背着两条人命、身揣巨款、潜逃两年的A级通缉犯,就藏在你管辖的这座城市里,像一颗随时会引爆的炸弹。抓,必须抓,而且要抓得万无一失。不能让他跑了,更不能伤及无辜,自己人也决不能出事。 负责这次抓捕行动的,是时任兰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刘晓林。老刘他们分析了乔立夫的所有资料,得出一个结论:这个人,极度危险。他不是那种冲动型的罪犯,他每一步都经过算计。而且,两年多的逃亡生涯,足以把任何一个人的神经磨炼得像钢丝一样,既坚韧又敏感,稍有风吹草动,他可能就会做出最极端的反应。 所以,必须雷霆一击。 计划定下来了:8名精锐刑警,组成突击队,对乔立夫实施抓捕。这8个人,都是局里身手最好、经验最丰富的老手。说“8对1”,听起来好像我们人多欺负人少,但只有当时的一线刑警才知道,面对乔立夫这种对手,任何轻敌都是在拿自己和百姓的生命开玩笑。 7月8日,天刚蒙蒙亮。兰州的一栋居民楼里,大部分人还在睡梦中。乔立夫就住在这里。他化名“李强”,以一个普通生意人的身份,安静地生活着。 8名刑警悄无声息地摸到了他的房门外。没有破门锤,没有闪光弹,那时候的抓捕,靠的就是一个“快”字。当房门被打开的一瞬间,8个人如猛虎下山一般扑了进去。 乔立夫的反应快得惊人。据说他当时几乎是瞬间就从床上弹起,企图反抗。但一切都结束了。在他做出任何有效抵抗之前,几双有力的大手已经死死地控制住了他的关节。整个过程,可能也就几秒钟。这位曾经让无数警察头疼的“微笑杀手”,在兰州的清晨,就这样落网了。悍匪落网,正义伸张,皆大欢喜。 但现在来看,这事儿没那么简单。这不仅仅是一个陈年旧案,更像一个时代的切片。它告诉我们,在那个技术相对匮乏的年代,我们的警察是如何办案的。 靠的是什么?是“人”本身。 是老刑警脑子里那张活地图,是他们走街串巷磨出来的直觉,是他们敢于在关键时刻和犯罪分子脸对脸、硬碰硬的血性。8对1,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学题,它背后是周密的研判,是对战友生命的负责,更是对犯罪分子的最大敬畏——没错,是敬畏。只有充分敬畏对手的狡猾和残忍,才能做出最稳妥的部署。 现在呢?我们有了“天网”。 前段时间有一个数据,说咱们国家重点公共区域的摄像头覆盖率已经达到了100%。一个犯罪嫌疑人,只要他出现在公共场合,他的一举一动都会被记录下来。大数据会迅速分析他的轨迹,锁定他的落脚点。别说潜逃两年,现在很多案子,都是24小时内人就抓到了。 这是科技的胜利,是时代的进步。它让犯罪分子无处遁形,极大地提升了我们的安全感。 但这种技术上的碾压,会不会让我们逐渐淡忘一些东西?比如,那种面对未知危险时,依然选择挺身而出的勇气;那种在没有“上帝视角”的情况下,依靠逻辑、经验和智慧,一步步从蛛丝马迹中拼凑出真相的坚韧。 今天的警察,面对的挑战和30年前已经完全不同。乔立夫式的悍匪少了,但新型犯罪,比如电信诈骗、网络黑客、金融犯罪,却越来越猖獗。犯罪分子的“武器”,从手枪变成了键盘和代码。我们和犯罪的斗争,战场已经转移了。 30年,弹指一挥间。兰州那座抓捕乔立夫的居民楼,可能早已淹没在城市更新的浪潮里。当年那8位英雄的刑警,也应该都到了退休的年纪,含饴弄孙,过着平静的生活。 而乔立夫,早已在1996年被执行枪决,为他的罪行付出了代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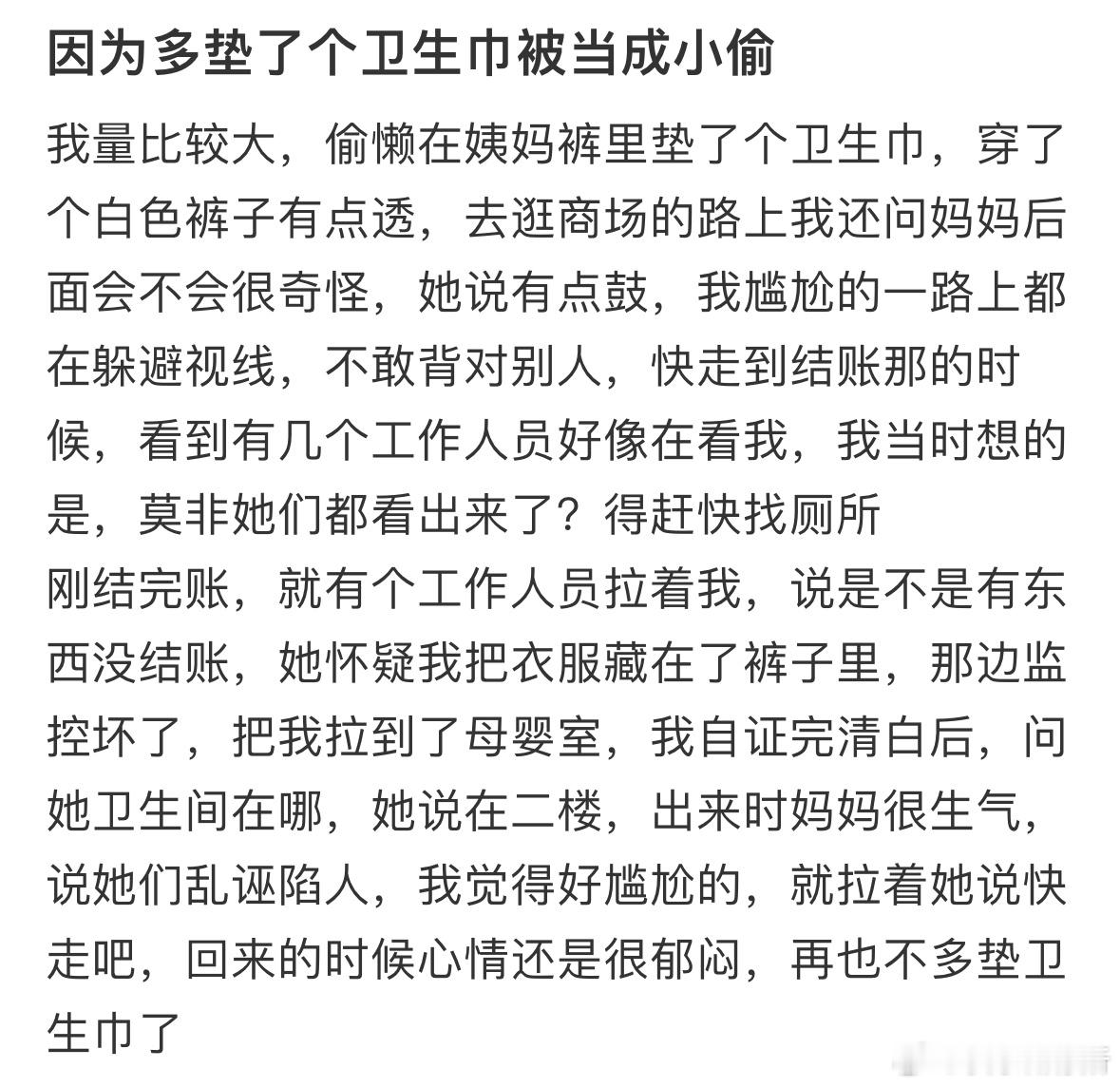
![[点赞]前段时间,央视曝光一个让全网震惊的新闻,近两年在缅北被大力打击后,国内](http://image.uczzd.cn/9019449669050563066.jpg?i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