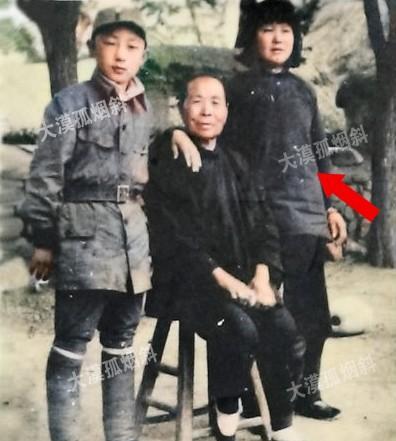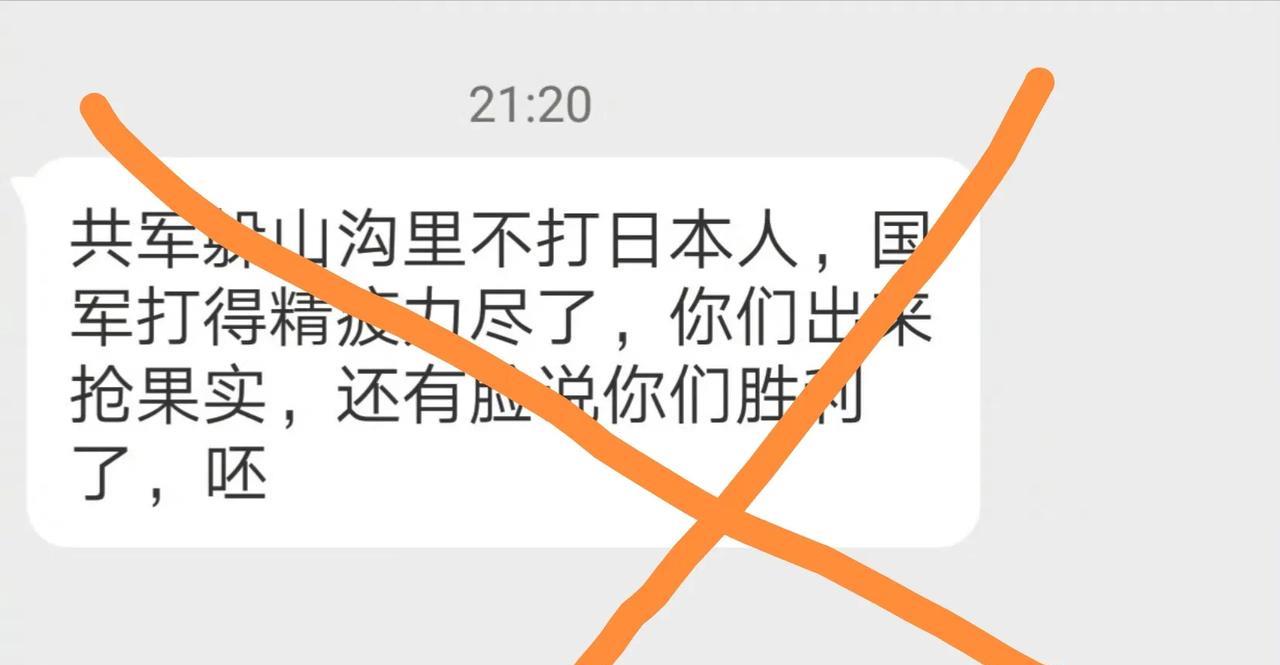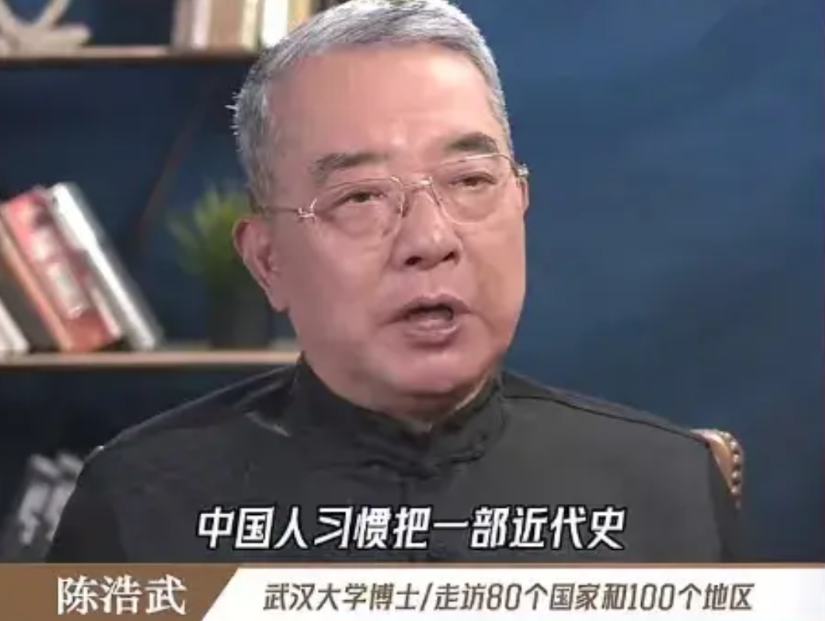“我去炸掉它!” 1962年11月,喀喇昆仑山脉的寒风像刀子一样刮过河谷,新疆军区某边防连的战士们正沿着结冰的河床执行穿插任务。 突然两侧山岩后传来震耳欲聋的枪声,密集的子弹瞬间在雪地上犁出一道道白线——他们闯进了印军精心布设的伏击圈。前后两个暗堡里的重机枪疯狂扫射,把连队死死压制在毫无遮蔽的开阔河滩上,远处已经能看到印军步兵的身影在蠕动,合围之势即将形成。 就在这要命的时刻,增援的九连一排从侧翼山腰摸了上来,但要撕开缺口,必须先拔掉正面那个吐着火舌的“铁疙瘩”。 “我去炸掉它!”一个年轻的声音在枪声中炸开,19岁的战士王忠殿已经攥紧了怀里的爆破筒,眼神在硝烟里亮得像星。 这场发生在加勒万河谷附近的遭遇战,是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无数惨烈瞬间的缩影。当时印军凭借对地形的熟悉,在喀喇昆仑的险要地段修了不少“地堡群”,这些工事大多利用天然岩石构筑,射孔刁钻,火力交叉,成了我军推进路上的硬骨头。 这次被伏击的连队本是要绕到敌军侧后,却没料到在河谷拐弯处撞上了预设阵地,正面暗堡里的机枪手显然是老手,子弹打得又准又密,三名冲锋的战士刚跃起就倒下了,整个连队被钉在原地动弹不得。 王忠殿和战友们赶到时,正看见河滩上的战友们趴在雪窝里艰难还击,排长急得用望远镜猛砸岩石。 那个要命的暗堡藏在一块大青石后面,射孔低得几乎贴着地面,常规爆破根本找不到角度,扔过去的手榴弹要么被岩石弹开,要么炸不到核心。 “这地形,上去就是活靶子!”有老兵低声嘀咕,零下二十多度的严寒里,大家的额头却全是汗。 王忠殿把棉帽往地上一摔,露出冻得通红的脸:“我个子小,能从石缝钻过去!”他是河南洛阳人,入伍刚一年,平时话不多,但摆弄爆破器材是把好手,训练时总缠着老兵问这问那。 谁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当时部队用的爆破筒是老式的,得手动拉燃引信,4.5秒的燃烧时间里,必须准确塞进目标才能奏效。 王忠殿把棉衣扣子解开,只穿件单衣匍匐前进,他说这样动作更灵便,可战友们看着他在雪地上挪动的身影,心都揪到了嗓子眼。 敌人很快发现了这个“小目标”,子弹嗖嗖地从他头顶飞过,积雪被不断溅起。离暗堡还有三米远时,他猛地一个翻滚躲到青石侧面,深吸一口气拉燃引信,用尽全身力气把爆破筒从射孔塞了进去。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意外发生了,印军士兵从里面把爆破筒推了出来,冒着火花的铁筒“咕噜噜”滚到王忠殿脚边。 引信已经烧到半截,滋滋的火花看得清清楚楚。没有丝毫犹豫,王忠殿一把抓住滚烫的爆破筒,再次狠狠塞进射孔,这次他用胸口死死顶住,任凭敌人从里面往外推。 战友们只听“轰隆”一声巨响,暗堡的火力瞬间哑了,浓烟裹着碎石冲天而起,而那个年轻的身影,永远定格在了堵住射孔的瞬间。 硝烟散去后,战友们冲到暗堡前,在废墟里找到了王忠殿烧焦的军帽,帽檐上还留着他用红漆写的“忠”字。这个19岁的青年,入伍才一年零三个月,牺牲前刚被评为“五好战士”。 他在日记里写过:“当兵就是为了保家卫国,死也要死在战场上。”这句朴实的话,成了他留给世界的最后誓言。 战后,部队为他追记一等功,追授“战斗英雄”称号,他的事迹很快传遍了边防部队,成了战士们口中“用胸膛堵枪眼的好兄弟”。 很多人不知道,当时我军的装备比印军差了不少。王忠殿用的爆破筒没有先进的延时装置,全靠手速和胆量;而印军暗堡里不仅有重机枪,还有美式卡宾枪,火力持续性强得多。 在海拔四千多米的高原上,连呼吸都费劲,更别说带着几十斤装备冲锋。可就是在这样的差距下,我军战士凭着一股“不怕死”的劲头,把印军的工事一个个拔掉 就像王忠殿的排长在战后总结里写的:“敌人靠的是钢筋水泥,我们靠的是战士的骨头硬。” 这场战斗也让部队看清了山地作战的短板。穿插时缺乏专业侦察设备,对印军“石砌暗堡+交叉火力”的战术不熟悉,导致多次陷入被动。 王忠殿的牺牲换来了宝贵的经验,此后部队专门研究了山地爆破战术,给爆破手配了更轻便的器材,还练出了“火力掩护+多点突击”的新打法。 这种从血的教训里钻出来的智慧,成了后来反击战节节胜利的关键。 如今在喀喇昆仑山脉的新藏公路旁,王忠殿的纪念碑就立在当年战斗的河谷边,碑身上“战斗英雄王忠殿”七个字被高原的风雪打磨得愈发清晰。 每年新兵上高原,都要到这里献束花,听老兵讲那个19岁的青年用身体顶爆破筒的故事。 2020年加勒万河谷冲突中,祁发宝团长张开双臂挡在战友身前的身影,让很多人想起了半个多世纪前的王忠殿。 这种刻在骨子里的血性,从来都是中国军人的“传家宝”。 资料:做“昆仑苍鹰”的守望人·全国党媒信息公共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