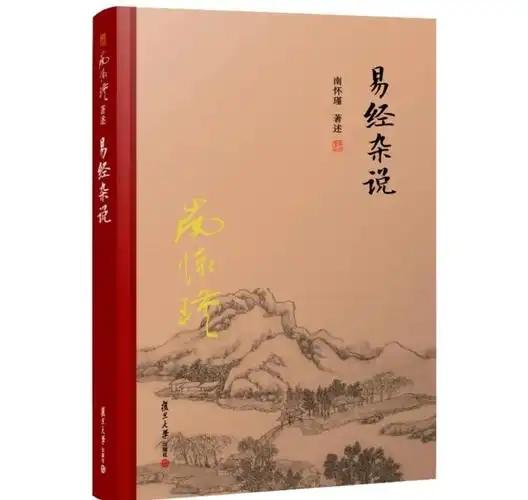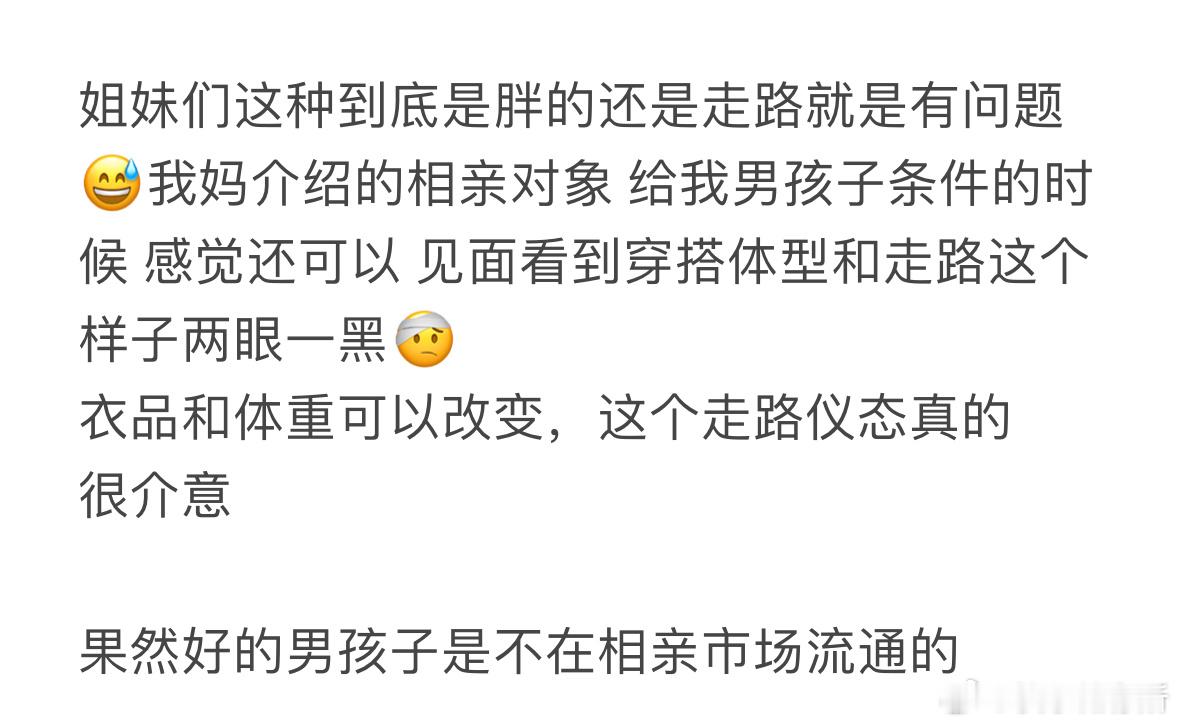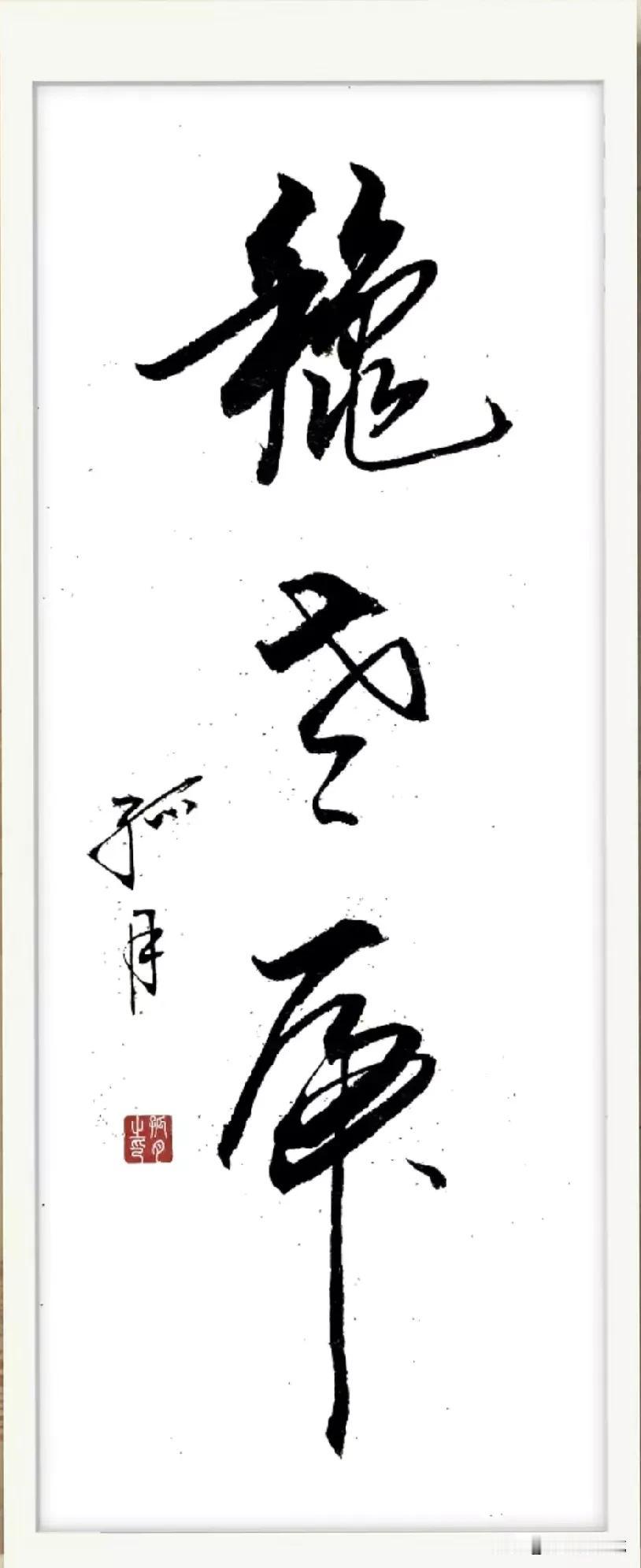清代大诗人龚自珍晚年迷上了赌博,输了好多钱,有一天给自己算了一卦,卦象是日进斗金,于是又去了赌场,志在必得。 道光二十年,在杭州城西一处破书斋内,48岁的龚自珍,此刻正对着几枚铜钱出神。 他屏息凝神,将铜钱掷下。 龟甲上,铜钱翻滚、停滞,最终呈现出一个吉卦“日进斗金”。 随即,他起身拉开书桌抽屉,取出一方色泽温润的古砚。 这东西可不一般,那是龚家数代相传的“守拙”砚。 他看了两眼,却狠下心,直奔城中盐商巨贾的深宅大院。 而他做的这一切只为了“翻身”,企图在赌桌上扭转半生潦倒的困局! 要说龚自珍的困顿,这和他所存在的腐朽王朝有着藕断丝连的联系。 道光十九年,这位在京城官场待了二十载的礼部主事,最终选择了挂冠而去。 六品微官月俸四两,这钱少的可怜,连为家人添置冬衣都得犹豫。 更令他窒息的,他屡次上书,针砭时弊,痛陈吏治腐败、民生凋敝,却石沉大海,还徒惹权贵与同僚排挤。 最终,他选择了辞官。 他雇了两辆简陋马车,一辆载书,一辆载人,将妻儿暂留京城,独自踏上了南归之路。 沿着京杭大运河缓缓南行,龚自珍第一次如此真切地触摸到大清帝国的脉搏与疮痍。 江苏清江浦,他目睹纤夫们在号子声中,将漕船一寸寸拉过闸口。 想到京城官署中自己每日所食的精米白面,正是这些骨瘦如柴的肩膀拖拽而来,一股巨大的悲怆与羞耻感瞬间攫住了他。 在扬州街头,烟馆林立,吞云吐雾的瘾君子形销骨立,与不远处林则徐在广东禁烟的壮举形成刺眼对比。 龚自珍心中五味杂陈。 途经一处大旱之地,百姓设坛祈雨,哀鸿遍野。 当地道士慕其闻名,恳请他为祭神作诗。 龚自珍胸中块垒郁积写下:“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这首日后被奉为时代最强音的《己亥杂诗·其二百二十》,此刻不过是他目睹民生疾苦、痛感朝野沉闷时,一声悲愤的呐喊。 然而,正是这趟放逐般的旅程,激发了他前所未有的创作激情。 他随身携带一只竹篓,每当心潮澎湃,思绪翻涌,便随手抓起鸡毛笔疾书。 写完,便将纸团随手掷入篓中。 待他回到杭州,已积攒了315个纸团,这便是彪炳史册的《己亥杂诗》。 然而,精神的丰盈无法填补现实的窘迫。 回到杭州的龚自珍,昔日名满天下的才子,陷入了经济困顿。 杭州盐商富甲一方,常在家中举办奢华宴饮,广邀名流,龚自珍作为文坛泰斗,自然在受邀之列。 宴后,宾客常在花园中以赌博为戏消遣。 起初,龚自珍只是偶尔参与。 但官场失意的郁结、经济拮据的压力、以及对现实无力感的逃避,如同无形的漩涡,将他渐渐拖入赌桌的深渊。 他渴望在牌局的输赢间,找到一丝掌控命运的幻觉,更幻想能一夜暴富。 然而,命运似乎刻意捉弄这位才子。 他逢赌必输,屡战屡败。 微薄的家底迅速耗尽,甚至不得不变卖珍藏的书籍字画。 每一次输光后,他都认为自己下一把“翻本”。 道光二十年那次赴宴前,他怀着近乎绝望的心情为自己卜卦。 当“日进斗金”的吉兆呈现时,他视传家宝“守拙”砚为最后的赌注,典当所得五十两银子,成了他孤注一掷的资本。 赌桌上,他全神贯注于每一次骰盅的起落、每一张牌面的翻覆。 然而,幸运之神并未眷顾。 五十两银子转眼输得精光,他甚至说服了仰慕他的举人王樾出资合伙,结果将王樾带来的数千两银子也一并输尽。 看着王樾错愕而无奈的脸,龚自珍羞愧的再也不敢想“翻本”的妄念。 他踉跄起身,不发一言,冲出赌场。 这场惨败,如同一盆冰水,浇醒了沉迷于赌桌幻梦的龚自珍。 他回到书斋,颓然瘫坐。 目光触及案头尚未完成的《病梅馆记》手稿,文中对束缚天性、摧残生机的控诉,此刻读来字字锥心。 他自己不也正是一株被时代与环境扭曲的“病梅”吗? 赌博非但未能解脱困境,反而让他离“守拙”的家训与“化作春泥”的初心越来越远。 他做出了决绝的改变,从此闭门谢客,婉拒一切可能涉赌的宴饮邀约。 他将全部精力重新投入到书院讲学与著书立说之中。 尽管生活依旧清贫,但精神的充实逐渐驱散了赌博带来的阴霾。 鸦片战争爆发后,年过半百的他四处奔走呼号,甚至写信给江苏巡抚梁章钜,请求亲赴前线效力,以一介书生之躯,践行“落红护花”的誓言。 然而,命运并未给他更多时间。 道光二十一年,龚自珍突发急病,溘然长逝,终年五十一岁。 他留下的,是《己亥杂诗》中那315颗璀璨的思想明珠,照亮了后来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志士的道路。 也留下了晚年沉迷赌博、典当传家砚台的尴尬印记。 这看似矛盾的两面,恰恰构成了一个完整而真实的龚自珍。 真正的“日进斗金”,不在赌桌的方寸之间,而在思想的星河璀璨与精神的薪火相传。 主要信源:(《龚自珍全集》中华书局、《清史稿·龚自珍传》中华书局、《清代官员履历档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