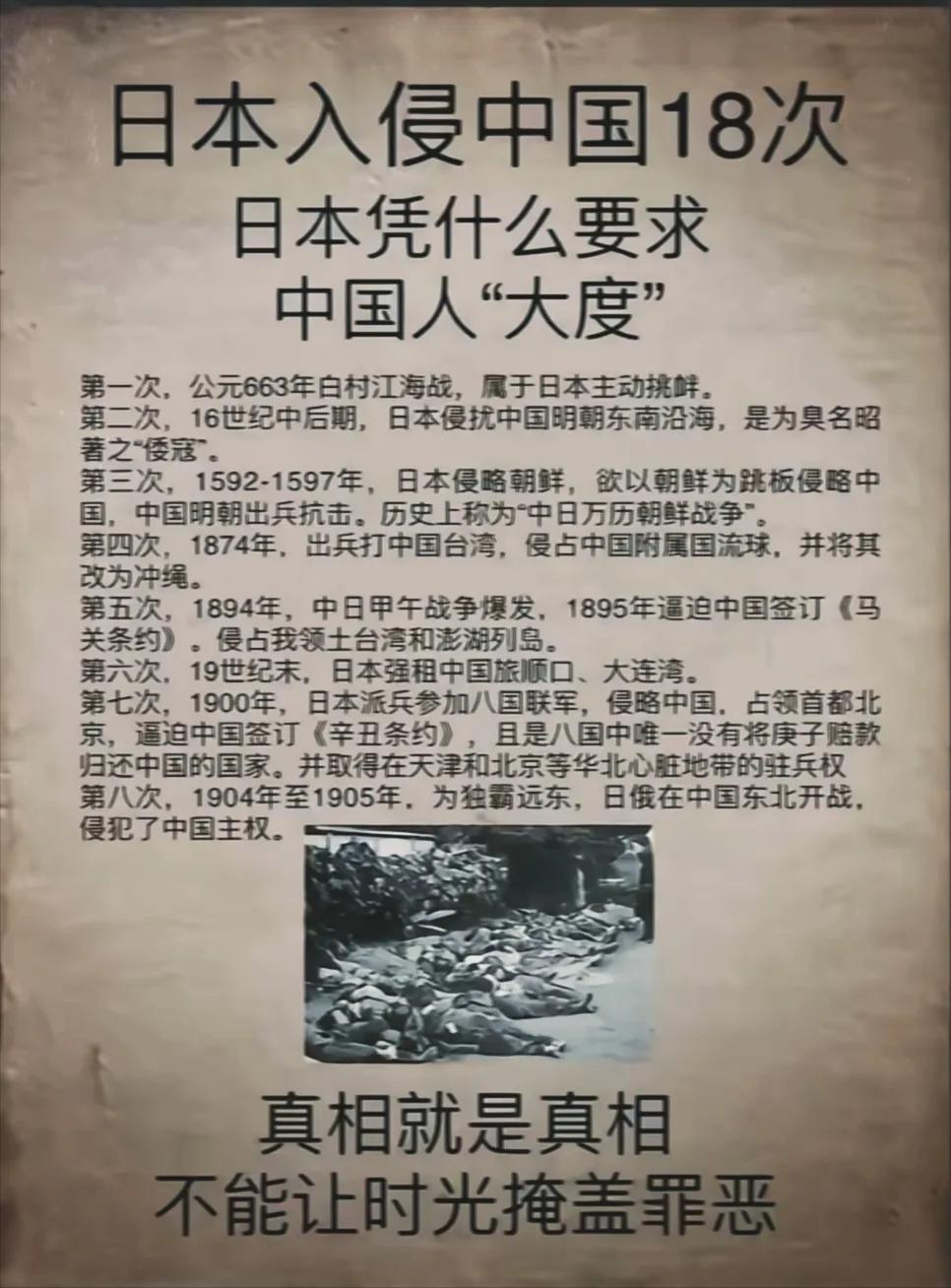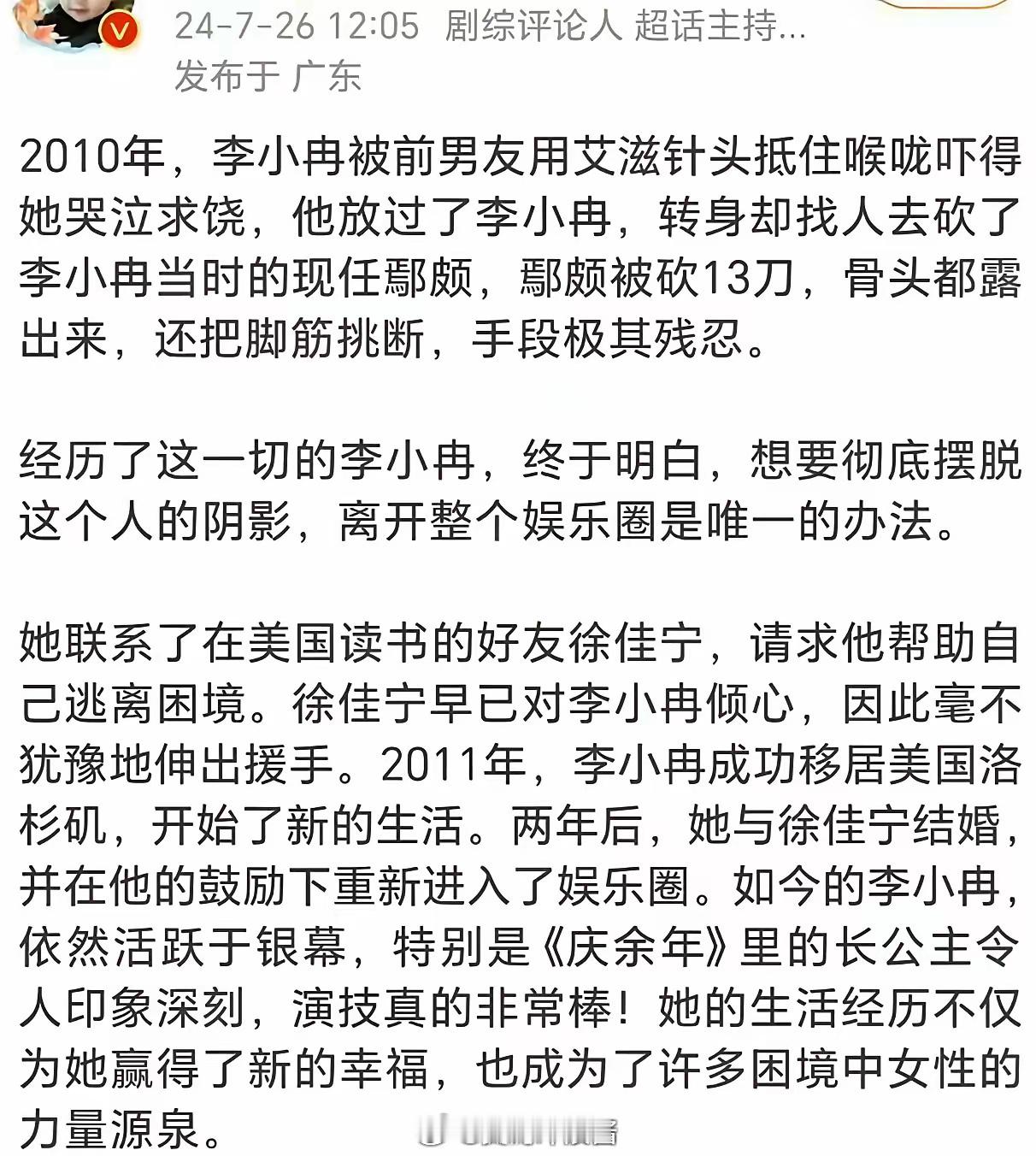大宋皇帝寝宫,宋太宗赵光义刚刚断气,余温还在。坐在榻上的李皇后擦干眼泪,突然对众人宣读:"皇上驾崩,立长子赵元佐即位,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大臣吕端赶紧跟上:"先帝已立太子,防的就是今天!" 寝宫里的烛火“噼啪”响了一声,把李皇后脸上的惊愕照得清清楚楚。她攥着衣角的手紧了紧,指甲几乎要掐进丝绒里——方才擦眼泪时还红着的眼眶,这会儿倒透出几分冷意。“吕相公这话是什么意思?”她声音压得低,却带着不容错辨的硬气,“元佐是皇上长子,又是我亲生的,立他难道不合规矩?” 这话抛出来,站在一旁的几个内侍都缩了脖子。谁不知道赵元佐的底细?当年太宗把弟弟赵廷美贬到房州,满朝文武没人敢说话,偏是这长子跪着哭了三天,说“叔叔无罪,父皇不能这么做”。 太宗气得把他关进府里,没过多久,他竟疯了——放火烧了自己的宫殿,见人就扔石头,后来虽好了些,可太宗早把他从继承人的名单里划了去。倒是三子赵恒,前年刚被立为太子,东宫的仪仗都按规矩备齐了的。 吕端站在离榻边三步远的地方,官帽上的缨穗垂着,纹丝没动。他看了眼榻上还留着余温的太宗,又转向李皇后,语气平得像摊静水:“皇后娘娘忘了?去年冬至祭天,先帝带着太子在圜丘行亚献礼,满朝文武都看着呢。太子印玺还在东宫的宝匣里锁着,先帝亲手题的‘皇太子宝’四个大字,墨迹都没干。” 李皇后的脸白了白。她不是忘了,是故意不提。赵元佐疯病那几年,她夜里抱着儿子哭,总怕他这辈子就这么毁了。后来元佐渐渐好了,她心里那点念想又活了——太子赵恒性子软,不像元佐带着股烈气,真要是元佐当了皇帝,她这当娘的,腰杆才能真挺起来。 方才见太宗咽了气,宫里乱成一团,她才敢咬着牙说这话,原以为凭着皇后的身份,总能压下去,没成想头一个站出来顶她的就是吕端。 正僵着,殿外忽然传来脚步声,是太子赵恒带着东宫的人赶来了。他一身素色袍服,头发都没来得及梳整齐,进门看见榻上的太宗,“噗通”就跪了下去,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掉,连哭都忘了出声。那模样看着实在可怜,有几个老臣跟着红了眼眶。 李皇后的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却被吕端抢了先。吕端走到赵恒身边,扶着他的胳膊起身,又转身对着殿里所有人朗声道:“先帝遗命,太子赵恒即帝位!谁有异议?”他声音不高,可每个字都砸在地上响。 站在李皇后身后的两个外戚刚想往前凑,被吕端扫过来的眼神一逼,又生生停住了——他们还记得,当年吕端当参知政事时,太宗说他“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今日看来,这话半点不假。 李皇后望着赵恒单薄的背影,又看了看吕端挺直的腰杆,忽然泄了气。她慢慢站起身,走到赵恒面前,福了福身,声音轻得像叹息:“既如此,便依先帝的意思吧。”话说完,眼泪倒真掉了下来,这次不是装的——她知道,元佐这辈子,是真没机会了。 后来赵恒登基,就是宋真宗。登基那天,吕端站在丹陛下面,看着新皇帝接受百官朝拜,忽然想起太宗临终前拉着他的手说的话:“太子仁厚,可性子软,往后朝堂上的事,你得多盯着。”他那时只躬身应了“臣遵旨”,此刻看着御座上那个还带着青涩的年轻人,才懂了太宗那话里的掂量。 有人说李皇后后来总在宫里念元佐的名字,有时还偷偷让人把东宫的点心送去元佐府里。元佐却不怎么见人,天天在府里种菊花,种了满满一院子。有回真宗去看他,他正蹲在地上浇花,抬头看见皇帝,也只是拱了拱手,没喊“陛下”,还像当年在宫里那样,叫了声“三弟”。 真宗站在菊花丛边,看着哥哥鬓角的白发,心里发酸。他想把元佐接进宫里住,元佐却摇了头:“我在这儿挺好,不用操心那些朝堂事,也不用记着谁是父皇的弟弟,谁是该贬的人。” 吕端后来告老还乡时,真宗去送他。路上问他:“当年在寝宫,若皇后执意要立大哥,您会怎么办?”吕端笑了笑,指着路边的石碑:“先帝立太子,就像把国号刻在了这石头上,谁想改,也得问问这天下人认不认。我不过是说了句实话罢了。” 石碑上的字被雨水冲得有些模糊,可“大宋”两个字,依旧看得清清楚楚。就像那年太宗断气的寝宫里,烛火虽晃,可太子的名分早定了,任谁想拧,也拧不过先帝的盘算,更拧不过朝堂上那点最实在的规矩。 参考书籍:《宋史·吕端传》《续资治通鉴长编·太宗至道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