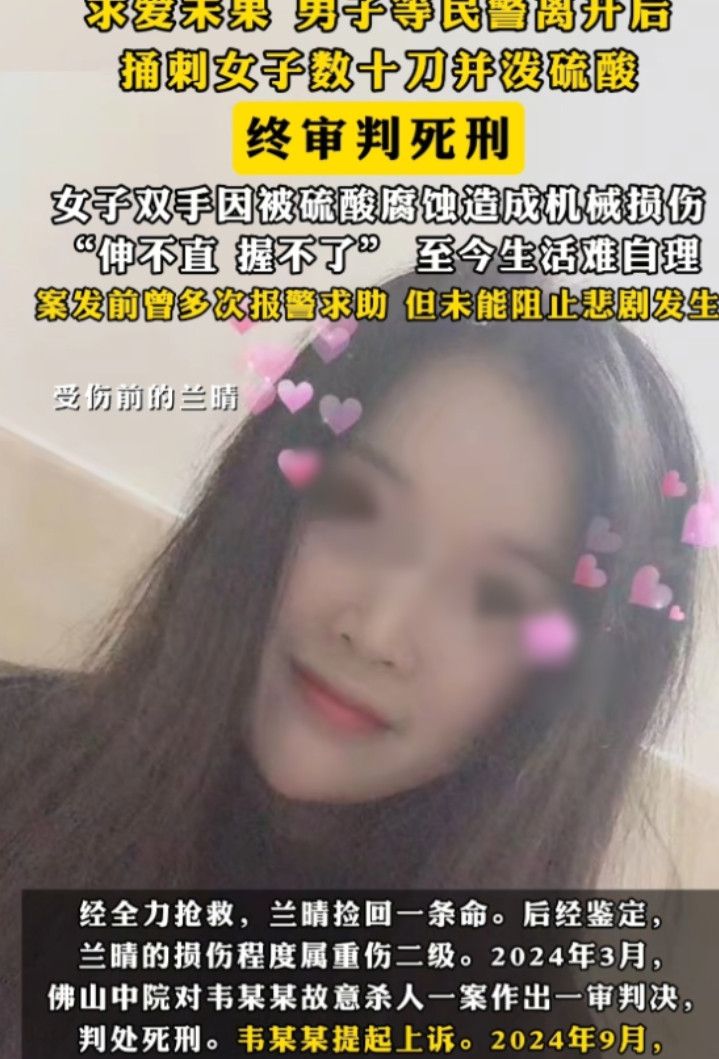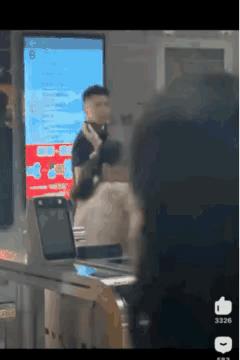广西,66岁男子与情人在酒店发生关系,情人睡醒一觉后,发现男子没了呼噜声,判断男子已经死亡,情人连忙离开酒店,一个小时后再次返回,要求工作人员一同查看男子的情况。事后,男子的家属将情人告上法庭,索赔55万。情人辩称,男子死亡时她还没睡醒,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回家是吃降压药的!法院这样判! 据酒店监控记录和李某的庭审陈述,事发当日下午 3 时许,张某驾驶私家车将李某接至酒店。两人登记入住后,直至晚间 8 时均未离开客房。李某在庭审中称,期间两人发生了亲密关系,之后张某表示身体疲惫,便卧床休息,很快发出呼噜声。李某则在客房沙发上闭目养神,不久也沉沉睡去。 次日凌晨 1 时左右,李某从睡梦中醒来,发现客房内异常安静。她走到床边查看,发现张某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往日规律的呼噜声消失无踪。“我伸手探了探他的鼻息,感觉没什么气息,又摸了摸他的皮肤,已有有点发凉。” 李某在法庭上回忆当时的情景,称自己因过度恐慌,未敢触碰张某的身体,也未拨打急救电话。 在确认张某失去生命体征后,李某匆匆整理了自己的物品,于凌晨 1 时 20 分独自离开酒店。监控显示,她离开时步伐急促,并未与酒店工作人员有任何交流。一个小时后,即凌晨 2 时 23 分,李某再次返回酒店,神色慌张地找到前台工作人员,称 “和我一起来的人好像不行了”,并要求工作人员一同前往客房查看。 酒店工作人员与李某到达客房后,发现张某仍躺在床上,已无生命迹象,遂立即拨打了 120 急救电话和 110 报警电话。急救人员到场后,确认张某已死亡多时,初步判断死亡时间超过 4 小时。 张某的家属在得知死讯后悲痛万分。在料理后事的过程中,家属从警方处了解到李某发现张某异常后曾离开酒店一小时,认为正是这一小时的延误,错失了可能的抢救机会。 “如果她在发现我父亲异常时第一时间报警或呼叫急救,或许还有挽救的可能。” 张某的儿子在法庭上情绪激动地表示,父亲虽年事已高,但平时身体状况尚可,只是患有高血压,一直在规律服药。家属认为,李某作为当时唯一在场的人,对张某的生命安全负有不可推卸的照顾义务,其擅自离开的行为构成了不作为的过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据此,张某家属将李某诉至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以李某 “未尽到合理的救助义务” 为由,要求其赔偿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 55 万元。 庭审中,双方围绕李某的行为是否存在过错、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展开激烈辩论。 李某的代理律师辩称,李某与张某属于自愿发生的婚外情关系,并非法律意义上的配偶或家庭成员,彼此之间不存在法定的扶养或救助义务。“两人是临时相约在酒店见面,属于松散的社交关系,李某对张某的身体状况并不完全了解,更无法预见其突发意外。” 对于离开酒店的行为,李某解释称,自己患有高血压病史,当时因过度惊吓导致头晕目眩,“感觉天旋地转,浑身发抖,根本无法冷静处理。” 她声称,离开酒店是为了回家服用降压药,待情绪稍作稳定后,才意识到必须返回处理,因此在一小时后回到酒店并通知了工作人员。李某的律师补充道,即使李某当时立即拨打急救电话,也难以改变张某的死亡结果,“医学鉴定显示,张某系突发急性心肌梗死,属于猝死,从发病到死亡的时间极短,抢救成功率极低。” 张某家属的代理律师则反驳称,无论双方关系如何,李某作为事件的唯一目击人,在发现张某失去生命体征后,负有基于公平原则和社会公德的救助义务。“她不仅未履行最基本的报警、呼救义务,反而选择逃离现场,其行为违背了善良风俗,也延误了可能的抢救时机,主观上存在过错。” 青秀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结合法医鉴定报告、酒店监控、当事人陈述等证据,于 2024 年 8 月作出一审判决。 法院认为,本案的核心争议在于李某对张某是否负有法定或约定的救助义务,以及其行为是否存在过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而构成过错侵权,需满足违法行为、损害后果、因果关系和主观过错四个要件。 法院指出,李某与张某之间系婚外情关系,并非法律规定的具有扶养、扶助义务的亲属关系,也不存在基于合同等约定产生的特殊义务。在这种临时性的社交关系中,双方虽共处一室,但李某对张某的生命安全并不负有法定的救助义务。 关于李某离开酒店的行为,法院认为,其在发现张某死亡后因恐慌而暂时离开,虽在道德层面存在可指责之处,但该行为与张某的死亡结果之间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法医鉴定报告明确显示,张某的直接死亡原因是急性心肌梗死,属于突发性疾病导致的猝死,其死亡具有不可预见性和快速性,“即使李某当时立即采取救助措施,也难以改变死亡结果的发生。” 最终,法院认定李某的行为不构成侵权责任,依法驳回了张某家属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