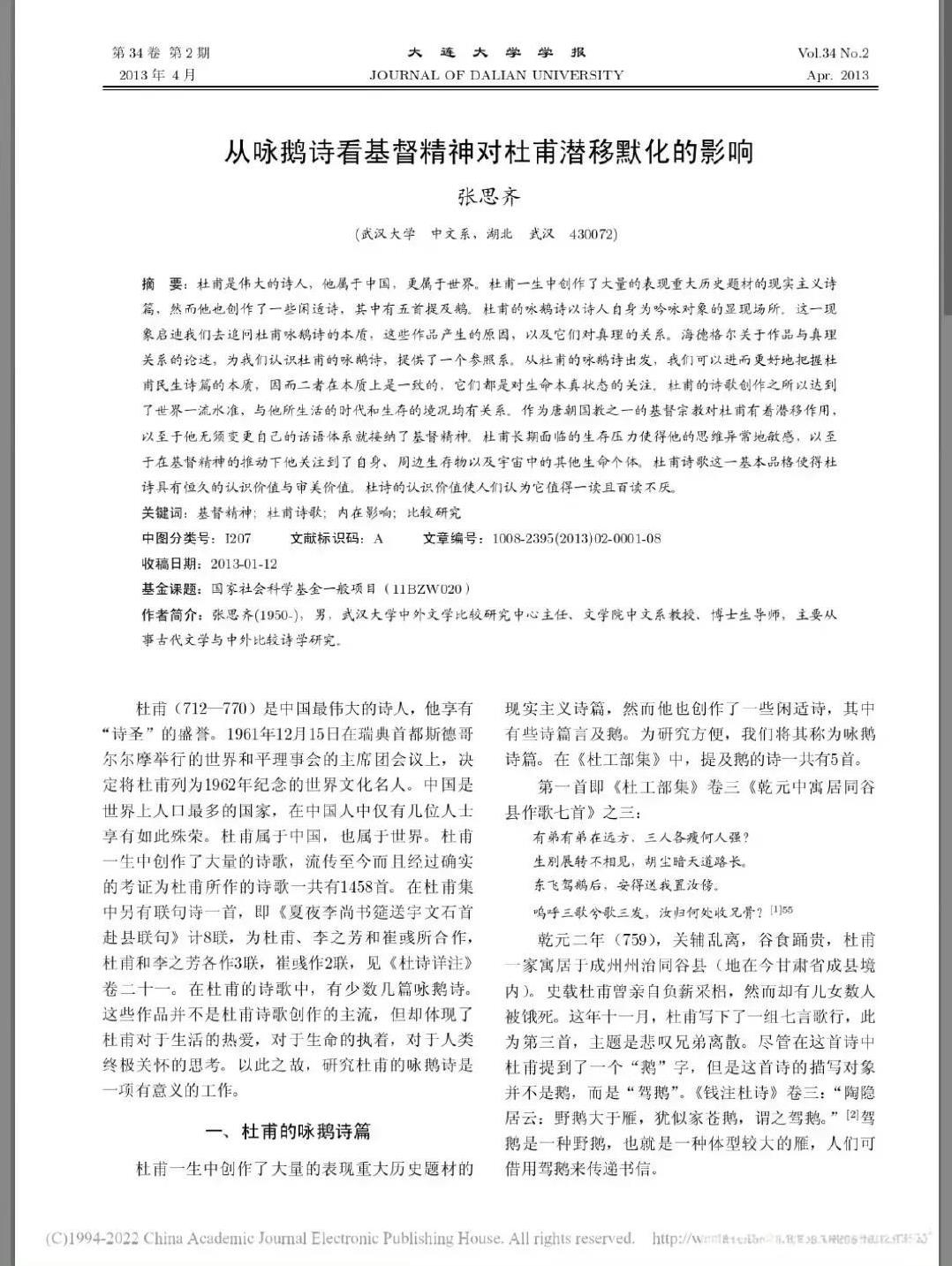宋美龄的六个奇葩嗜好,一般人都受不了!宋美龄出生在1898年的上海,那是个富裕
宋美龄的六个奇葩嗜好,一般人都受不了!宋美龄出生在1898年的上海,那是个富裕的基督教家庭。她爸宋嘉树早年去美国留学,回国后做生意,还推广基督教。她是家里最小的一个,上面有两个姐姐,宋蔼龄和宋庆龄。小时候住在上海租界,接触不少西方东西。宋美龄,是那个站在权力中心、活了106年的传奇女人。但很多人不知道,表面光鲜亮丽的第一夫人,私下其实有六个谁听了都得皱眉的“奇葩嗜好”。而这些爱好,大多不是“高雅”范畴,而是极致个人化,甚至让旁人难以忍受。第一个嗜好,让人直呼“作”:她对芒果严重过敏,却偏偏爱吃。吃完身上起大片风疹,痒得发疯。但她照吃不误,还让人准备好抗过敏药,等她吃完马上服下。不是一次,而是常年反复。明知道吃芒果过敏,她也不克制——在旁人看来像自虐,但她就是不肯戒掉。这不是普通嗜好,而是带有点偏执的“爱”。第二个嗜好,则更带画面感:她常在半夜吃火鸡骨头。不是吃火鸡肉,而是啃骨头。深夜十二点以后,女仆得随时准备她专属的火鸡骨头盘,一旦她兴致来了就要啃上一阵。安静黑夜里,传来啃骨声音,一屋子人谁都不敢睡死。蒋介石对此毫无办法。这个习惯延续几十年,哪怕搬到纽约晚年豪宅,她依旧改不了。有人怀疑她是因为童年营养不良留下习惯,但事实是她从小锦衣玉食。这就纯属“奇”,没理由,改不了。第三个嗜好,是抽烟。不时抽、不是偶尔,是“成瘾”。宋美龄二十多岁就开始吸烟,虽然不在公开场合表现,但身边人都知道她烟瘾极大。抗战期间事务繁忙,压力极大,她一天得抽上好几支,香烟成了稳定情绪的工具。蒋介石极其反感她吸烟。两人为此吵过不少次。蒋是“儒家式”男权代表,认为女性不该抽烟、不该晚睡。但宋美龄是那种愈压愈强的性格。越禁止,她越沉迷。这个“抽烟爱好”一直延续到蒋晚年。直到丈夫去世,她才真戒了烟。原因不是健康,而是“没人再烦我了”。这种背后心理,是她个性中最真实的写照。第四个嗜好是“娱乐沉迷型”:麻将、象棋样样不落。很多人以为,宋美龄一直是那个站在台前、英文演讲的铁腕夫人。但其实她闲暇时间最大乐趣,就是打麻将。抗战时重庆,台湾岁月,乃至赴美之后,她都保留“晚间麻将时间”。每次打上三四小时,谁劝都不听。象棋也爱。常年与幕僚或姐妹对弈。她性格争强好胜,赢棋就高兴,输棋就生气。有时输两局不上桌三天,连身边人都感到“难伺候”。这种投入,甚至超过了她对很多外交活动的兴趣。第五个嗜好,跟她留美背景脱不开——她是“好莱坞电影迷”。从年轻时读书起,她就习惯看西方电影。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能看进口电影是极大奢侈,但宋美龄几乎场场不落。她偏爱浪漫爱情片与惊悚悬疑片,尤其喜欢克拉克·盖博、凯瑟琳·赫本等演员。重庆时期,即使战火不断,她也要组织放映会。女兵、秘书、随从都得陪着看电影,哪怕外头防空警报拉响也不暂停。有人说她用电影逃避现实,也有人说这是她对西方生活的怀念。两者可能都有。她看电影从不是消遣,而是“沉浸”。有时候看完还写笔记,分析角色,评论剧情。在台湾时,她依旧保持“每周必看片单”。即使年事已高,也坚持坐轮椅去影院,或者在家安排胶片放映。这种对影像的执着,远超常人。而这也解释了,她为什么对电视、摄影、新闻镜头极度敏感。她知道镜头对形象的重要。第六个嗜好,是所有幕僚最怕的——她晚睡。不是偶尔熬夜,而是彻底夜猫子。每天凌晨两三点才睡觉,早上起床也晚。蒋介石一早五点起床诵经,她还在床上没醒。两人生活节奏完全错位,但宋美龄从不改作息。夜深人静,她觉得才是属于自己的时间。夜晚是她思考、看书、写字、抽烟、啃骨头、打麻将的时间。幕僚们都被她的作息搞到崩溃。没有人知道她何时要召见、何时开会、何时让人放映电影。一天时间表完全围绕她情绪展开。有人统计,她最晚的一次办公是凌晨四点。而她这样生活几十年。纽约老年阶段依旧不改,一直维持夜间清醒模式。这一点,也像她的一生——不走寻常路,越是不符合常规,她越能从中找到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