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粟裕进京汇报工作,李克农知道后,立即跑了过去,急切地问道:“粟裕同志,我的小儿子是不是在前线牺牲了?” 李克农是情报战线的老资格,向来沉稳。能让他失态的,只有家里的事 —— 他在问三儿子李伦。 李伦是 1947 年上的前线。那年在山东临沂,20 岁的李伦穿着一身不太合身的灰布军装,站在华野特种兵纵队的队伍里。 他拉着父亲的袖子,压低声音说:“爸,我改名叫李力了。到了部队,我不给您丢人。” 李克农当时板着脸:“上了战场,别当孬 种。” 说完转身就走,走到拐角处,偷偷抹了把脸。他知道,这一别,能不能再见都不好说。 从那天起,李克农多了个习惯。 每天看情报部门送来的阵亡名单,一个字一个字地扫。孟良崮、淮海、长江边、舟山群岛…… 只要看到 “李力” 两个字,心就像被攥住一样。 1950 年 2 月,有人来报,舟山战役结束了。 正在开朝鲜战争情报会的李克农,手里的钢笔 “啪” 地掉在桌上。他盯着地图上的舟山群岛,一动不动坐了二十分钟,烟灰掉在文件上,一点没察觉。 秘书后来回忆,那是他第一次见首长这样。 粟裕接到李克农电话时,正在总参谋部说华东防务的事。 “李伦?” 粟裕拿着电话琢磨,“华野特种兵纵队…… 陈锐霆那边有没有个叫李伦的营长?” 电话那头,陈锐霆马上回话:“粟司令,特纵确实有个李伦,榴炮团一营的,刚在舟山战役立了一等功。” 粟裕心里一下亮了。 1947 年建特种兵纵队时,他专门交代过,所有干部隐去家庭背景,防着国民党特务搞小动作。李伦改名叫李力,他这个司令员都不知道。 “克农同志,三天内,我保证让你见到李伦。” 粟裕在电话里说得肯定,挂了电话却在想,这小子瞒着身份,在前线到底干了些啥? 这时候,李伦正在南京汤山炮校。 他是新中国第一批炮兵指挥员,正对着苏联顾问带来的喀秋莎火箭炮资料发呆。铅笔在沙盘上画着弹道,一笔一划,没敢分心。 警卫员闯进来:“李营长,华东军区急电!” 电报就四个字:速回南京。 李伦心里咯噔一下,赶紧往回赶。一见到陈锐霆,就被劈头问:“你小子,是不是李克农的儿子?!” 李伦愣住了。 原来粟裕问起李伦时,陈锐霆翻遍了档案才发现,这个在舟山战役里搞出 “机动炮群战术” 的功臣,竟是李克农的独子。 1949 年 8 月打大榭岛,暴雨下了一天一夜,李伦带着榴炮营,对着国民党军阵地轰了 12 个小时,把三个炮兵阵地全端了。 1950 年 5 月解放舟山本岛,他指挥的炮群精准打哑了敌军机场,登陆部队没受多少阻碍就上了岛。 这些事,他从没跟人提过家里的情况。 1950 年 3 月 15 日,北京饭店会客厅。 李克农来回走着,皮鞋踩在地板上,声音格外响。门一开,一个穿少校军装的年轻人站在那儿,胸前的勋章晃得人睁不开眼。 “爸……” 李伦刚开口,声音就卡壳了。 李克农盯着那枚一等功勋章,抬手就给了他一巴掌。 门外的警卫员吓了一跳,刚想进去,就见李克农一把抱住儿子,肩膀抖得厉害:“你个浑蛋,让老子担了三年心!” 那天晚上,父子俩沿着什刹海走。 月光把影子拉得老长。李伦说,在舟山群岛,为了藏炮位,他带着战士用芦苇编伪装网,编得满手是泡。 为了打准敌舰,他爬上桅杆看弹道,海风把衣服吹得像面旗子,脚下晃得站不稳。 “有次炮弹打光了,我带着炊事班,把迫击炮改成榴弹炮。” 李伦笑了,“那些国民党兵,估计以为我们会变戏法。” 李克农突然停下:“知道你为啥叫李伦不?” “你出生那天,我正破译国民党的‘围剿’计划,窗外有个卖糖葫芦的喊‘李伦 —— 李伦 ——’,我就记下来了。” 1955 年授衔,李克农成了上将,李伦站在队列里,肩上是少校军衔。 毛主席握着李克农的手:“你这个当爹的厉害,儿子更厉害!” 李伦望着父亲鬓角的白头发,想起三年前临沂火车站那个抹泪的背影,眼睛一下子就湿了。 后来,李伦成了新中国军事交通战线的带头人。 他主持修的川藏公路军用支线,1962 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物资全靠这条路往前送。 他参与设计的长江水下隧道,到现在还是战略物资运输的要道。 1988 年,李伦被授予中将军衔,胸前的勋章比父亲当年还多。 这段三年的寻子故事,成了革命史上的一段闲话。 说的是一个情报首脑的铁汉柔情,更是那代人的选择 —— 家在心里,国在肩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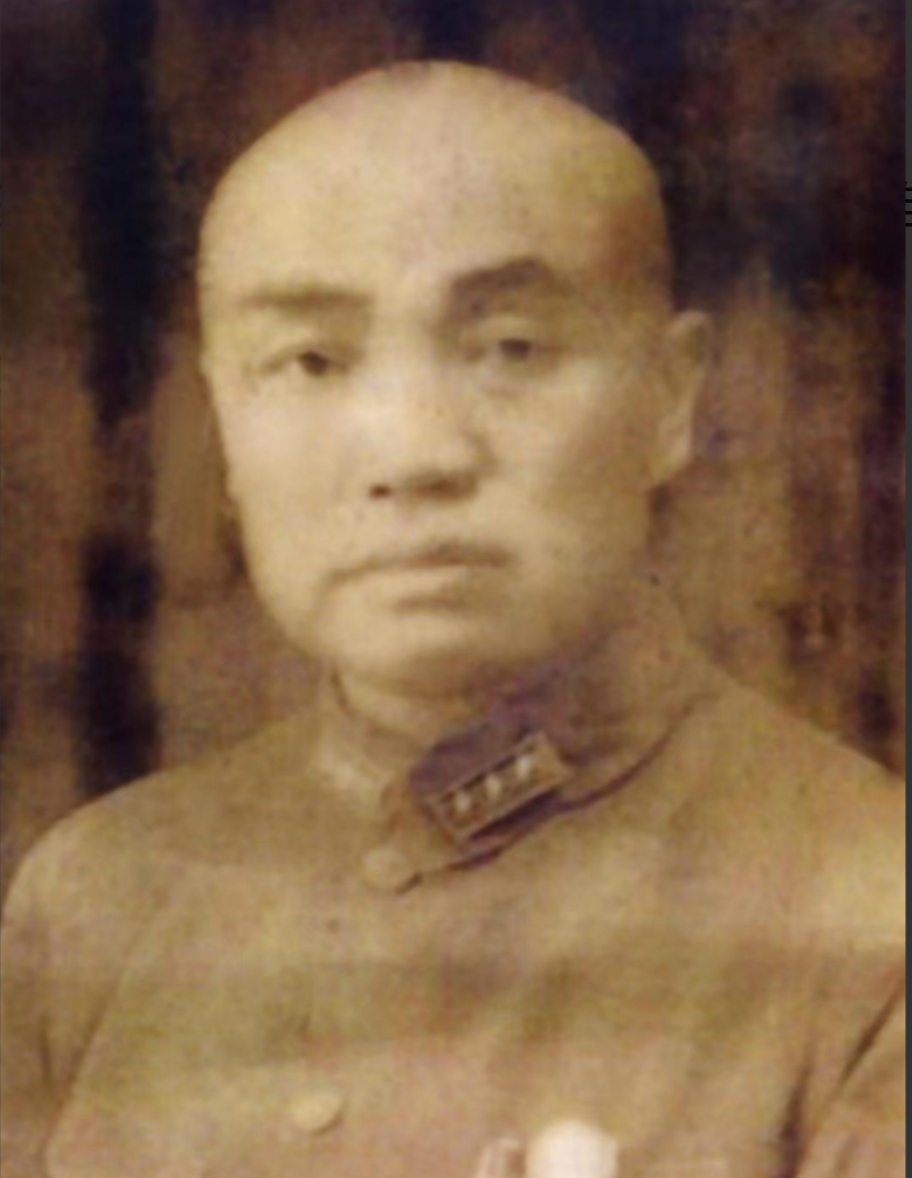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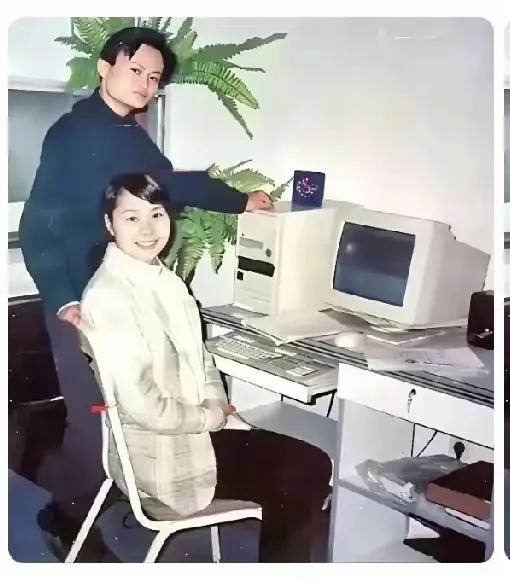
![里根总统用石油,干垮前苏联!特朗普这是学里根总统,用石油干垮俄罗斯吗?![捂脸哭]](http://image.uczzd.cn/9997198250089616420.jpg?id=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