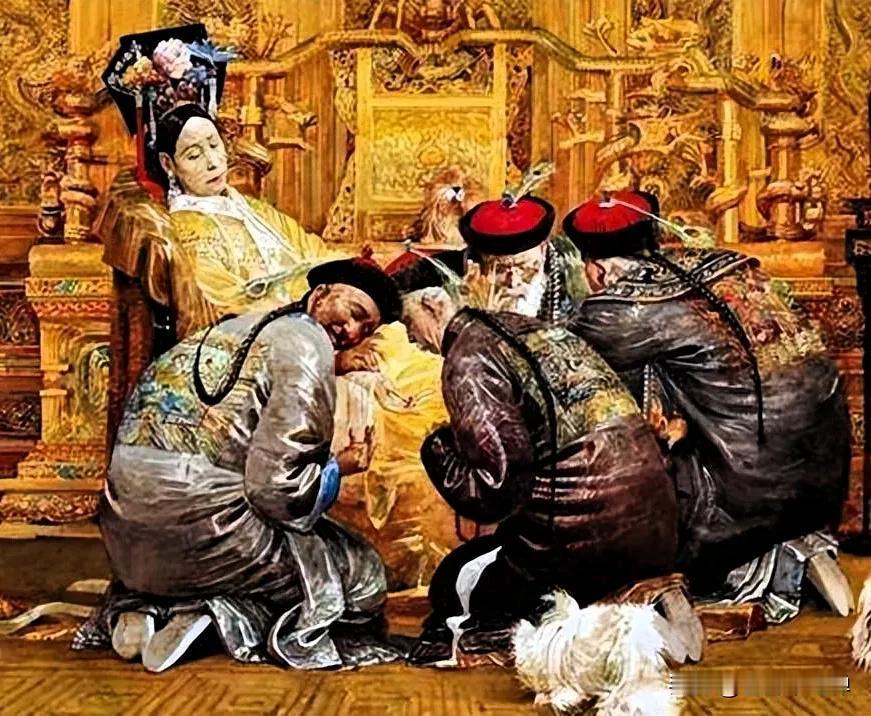道光十七年,两江总督陶澍回安化老家祭祖,途中停留醴陵县。总督大驾,醴陵县令受宠若惊,他来到渌江书院,找到在书院担任山长的左宗棠,求墨宝一副,送于陶澍。 左宗棠那时刚过二十五岁,在渌江书院做山长不过两年。听县令说明来意,这位日后名震朝野的“今亮”,脸上却没多少受宠若惊的神色。他铺开宣纸,蘸墨时手腕悬得很稳,笔锋落纸时却带着股少年人藏不住的锋芒。写的是副对联,上联“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下联“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 送联那天,陶澍在醴陵行馆刚歇下脚,就见县令捧着个卷轴进来。他本是随口应着,目光扫过联语时却猛地顿住。“印心石”是他少年时在安化老家书房的旧物,这等私密往事,一个湖南小书院的山长怎会知晓?再看“八州子弟翘首公归”,既点出自己总督两江的辖地,又藏着乡邻盼归的温情,字句里的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 陶澍当即让人去请左宗棠。两个年龄差了三十六岁的人,在行馆里一谈就是整夜。陶澍说起治理黄河时的艰难,左宗棠就接话讲湖南水系的特性;陶澍叹新政推行受阻,左宗棠竟拿出早就画好的舆图,指着上面的山川河道说:“两江富甲天下,却困于漕运,若能引湘入赣,开通水路,未必不是破局之法。” 谁也没想到,这场萍水相逢竟成了忘年交的开端。陶澍临走前,拉着左宗棠的手说:“我儿子陶桄,就托付给你了。”后来左宗棠果真收陶桄为弟子,在安化陶家教书八年。那八年里,他翻遍了陶澍收藏的典籍、奏折、舆图,把两江的民生吏治摸得比本地人还熟。 有人说,左宗棠后来能在东南沿海抗击法军,在西北收复新疆,那些运筹帷幄的本事,早在醴陵那副对联里就露了端倪。他写“印心石在”,是看透了陶澍的文人底色;写“八州翘首”,是摸准了封疆大吏的为政初心。一副对联,藏的不只是文采,更是识人知世的通透。 陶澍回安化祭祖后不到三年就病逝了。临终前,他给道光皇帝上了道奏折,里头专门提到“湖南举人左宗棠,才可大用”。那时左宗棠还在乡下种地读书,这份举荐,像一颗埋在土里的种子,要等十几年后才破土而出。 后来左宗棠率军收复新疆,路过安化,特意去了陶家旧宅。看着书房里那块“印心石”,他想起当年在醴陵行馆的彻夜长谈,提笔补了半阙词:“卅载交情,历艰难世事,到此方知真味。”墨迹落在纸上,晕开时像极了当年渌江水的波纹。 参考书籍:《左宗棠年谱》《陶澍评传》《清稗类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