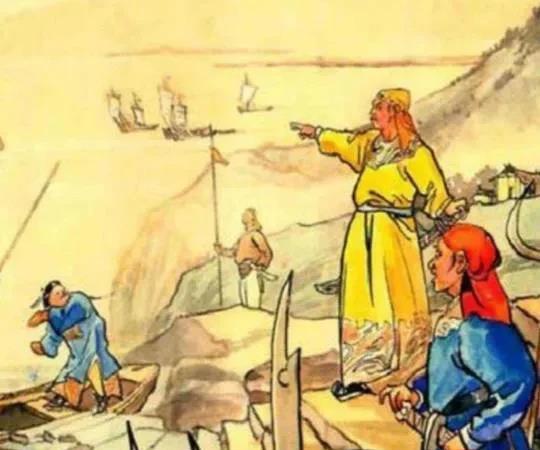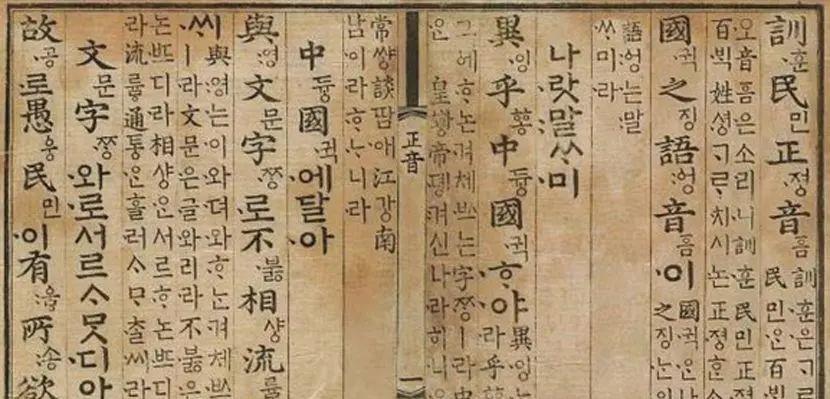1985年,中央军委提出了“军队要忍耐”的重大决策,财政只管拨六成军费,其余四成由军队自行筹集。那一年有430万军人,总共获得56亿美元拨款,而台湾的军费是98亿美元,日本的军费更是达到240亿美元,海军方面大量老旧型号舰艇不得不超期服役,舰艇状态普遍不佳且失修严重。日本媒体公开放言:“半小时消灭中国海军!” 1985年春天,北京西山的空气还有些凉,军委扩大会议在那年5月悄悄召开,坐在台上的人神情都不太轻松。 改革开放已经推开七年,全国上下都在琢磨怎么把饭碗端稳、钱包鼓起来。 经济建设成了头等大事,军队这个庞然大物的财政支出,自然也就被挤到了次要位置。 那年,中央定下一个基调:军队要忍耐,要服从大局。话说得沉稳,背后的现实却异常尖锐——国家只能承担军费的六成,剩下的四成,军队得自己想办法。 这不是一个小问题。全军四百三十万人,国家只拨了56亿美元。这点钱,不说发展装备,连养活人都紧巴巴。要知道,同一年日本的军费是240亿美元,台湾也有98亿美元。 更别提那些老掉牙的舰艇,很多本来该退役的军舰还在海上熬着,发动机轰得像喘不过气来的老牛,掉漆的舰身每一寸都在提醒人们:穷,是个不能忽视的战略问题。 军费吃紧,部队就得动脑筋。 1985年下半年,一份名叫《关于军队从事生产经营和对外贸易的暂行规定》的文件在军中流传开来。字面意思很清楚:军队可以经商了。 这项政策的落地,说白了,就是军队自己赚钱养自己。 那年头,全国都在下海,经商成了全民趋势,部队也就顺势跳入了市场的洪流。 最初的设想很朴素,无非是部队自己种些地、办些厂,给战士们改善伙食,顺便补贴点训练开支。 但现实很快走向了另一条路。 不管是前线部队还是后勤单位,几乎都开始搞经营,有的开运输公司,有的办外贸出口,连医院都开始搞创收。军属企业像雨后春笋一般冒出来,从北京到云南,从东部沿海到西北边陲,到处都是部队办的商贸公司、进出口公司、旅游公司。 这股风潮里,有的军区成立了自己的航空公司,有的军队在口岸开起了“特殊通道”。 军队经商从一开始就带着一种天然的优势:资源、人手、组织、纪律全都有。 而最关键的,是那一身军装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通行证。地方商人要跑三年关系的项目,军队往往打一个电话就能敲定;别人需要盖章走流程,军队车队可以一路绿灯直通港口。 问题就出在这种“太方便”上了。 很快,一些灰色交易浮出水面。军队企业开始涉及走私、逃税,甚至有些部队直接动用武器运输“特殊货物”。广东那几年,海关和边防曾多次拦截军车夹带私货的事件,背后都是用军车护送走私电器。 东北的一个后勤仓库,夜里变成了临时中转站,白天是军需,晚上是“货栈”。 而基层战士的训练情况,也因为经商而逐渐荒废。 有的部队士兵白天拉货送货,晚上在剧组拍戏当群演;军事基地被租给影视公司拍武侠片,操场成了江湖大堂,连枪械训练都被迫让位给道具布景。 士兵们一个月三十天,有二十九天没穿军装,真上演习场,连跑三公里都气喘吁吁。 军队之间,也因为利益问题开始内耗。 哪个单位的企业更挣钱,哪个将领掌控的公司更多,就更有发言权。 一些原本铁打的战友情,被生意场上的勾心斗角替代。部队之间明争暗斗,争摊位、抢资源、拼关系,演变成现实中的“军队企业大战”。 训练计划被拖延,士兵管理日趋松散,战斗力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下滑。 群众的观感也发生了变化。 一开始,老百姓还对“解放军下海经商”感到新奇,觉得是为国家分忧。 可当一些部队用军车强占地皮、军官带兵去敲商户门要摊位、娱乐场所挂上“军办”的招牌后,原本那个亲切、朴素、纪律严明的军队形象开始崩塌。 从社会层面来看,军队经商造成了非常明显的不公平竞争。 一个地方两个饭店,一个军队开,一个民间办,税收、物资、资源、甚至电价都不一样。民间企业生存越来越难,而军队的生意越做越大,甚至进入了金融、房地产、能源等关键行业。 这些现象,引起了不少高层将领的警觉。 张爱萍、秦基伟等人多次在军内会议上发出警告。 张爱萍提起宋朝靖康之耻,说得痛心疾首。他直言:一旦军队为了挣钱而废弃训练、淡忘职责,到最后不是敌人打不过,而是自己先散了架。 他的那句“该杀谁的头?先杀我们这些当官的”在军内流传了很久,不少人听了都沉默不语。 但说归说,做起来却不是那么简单。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虽然国家已经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也开始试图收缩军队的经商范围,比如禁止作战单位搞经营,划定“军企”和“战力”之间的界限。 但这些动作更像是补丁,无法从根本上遏制利益链的蔓延。 直到1998年,局面才迎来真正的转折点。 这一年,江泽民在军委会议上痛下决心,提出“军队必须退出经商”。 随后,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文,宣布全面禁止军队、武警部队、政法机关从事经营活动。 一句话,退场,没有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