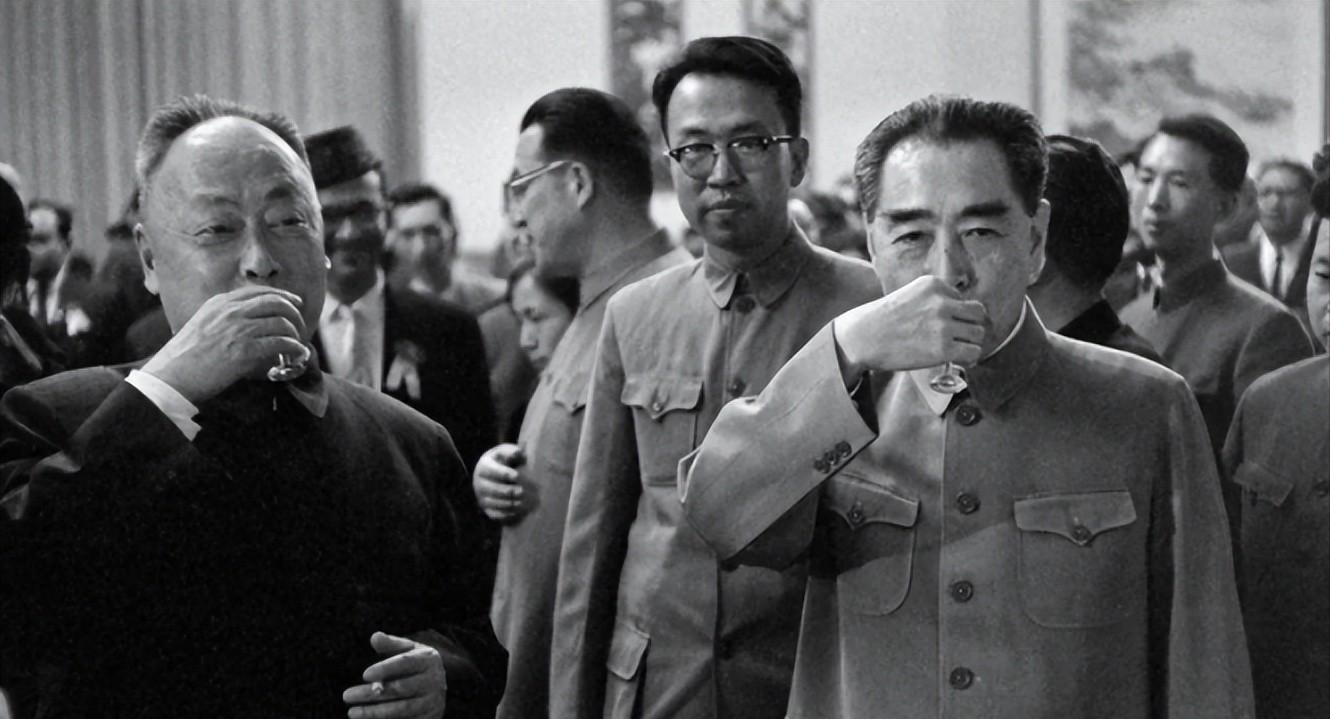1949年,谢晋元的遗孀向陈毅要了一个房子,陈毅就把吴淞路466号送给她,几天后,有人举报:她带了七八个年轻男人住进去,行为很可疑。 上海刚解放没几天,吴淞路466号那栋洋楼,大门紧闭。 可左邻右舍,都在默默关注着这个院子。 为啥? 因为新市长陈毅刚把这好宅子,送给了抗日名将谢晋元的寡妇凌维诚。 按说这是好事儿,可没过几天,怪事儿出来了。 这凌寡妇,咋领回来七八个汉子,住进去了?还同进同出! 街坊们都说这寡妇怕不是有啥见不得人的勾当? 但是有时候,没有亲眼所见,就不能乱说啊! 凌维诚是谁?那可是正经八百的苦命人! 她男人谢晋元,当年带着“八百壮士”死守上海四行仓库,跟小日本鬼子血战四天四夜,打出了中国军人的骨气! 后来撤退到租界,叫洋鬼子缴了械,待在了“孤军营”。 再后来,谢团长硬气因为没和汪精卫那帮汉奸勾搭,1941年叫杀手给害了! 这一下,只能凌维诚拉扯着四个娃,从广东那穷乡僻壤,一路千辛万苦回到上海。 他们想着来到上海滩,总能寻条活路吧? 哪知道,国民党那帮官老爷,嘴上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啥“抗战英雄遗属”,啥“党国不会忘记”,可实际呢? 给的抚恤金,那叫法币,贬值的比纸还快,买不了三袋白面! 凌维诚拖儿带女,求告无门,差点当乞丐! 凌维诚这女人,心善,重情义! 她忘不了男人的遗言,更忘不了自个儿在那些伤残老兵跟前撂下的话:“团长走了,我这个团长夫人还在!只要我有一口气,就不能叫你们流落街头!” 可这话说出来容易,做起来,难比登天! 战后的上海,乱得跟一锅粥样。 凌维诚咬着牙,她一个妇道人家,拖着娃,硬是走街串巷,钻桥洞,扒窝棚,去找那些散落各处的“八百壮士”。 那场景,瞅着就叫人掉泪! 苏州河的桥洞底下,她找着了当年的机枪手老赵,眼珠子被鬼子崩瞎了,如今靠过路人施舍口吃的活命! 银行大楼后身的垃圾堆边,她撞见一个烈士的寡妇,领着仨娃,正扒拉烂菜叶子呢。 这些老兵,当年都是铁骨铮铮的汉子,如今落得这下场,有的残了,有的叫鬼子抓过,只能在码头扛大包,在街上拉洋车,挣口饭钱。 凌维诚瞅着,心跟刀绞样疼! 光瞅着不中, 凌维诚把牙一咬,把心一横! 她先是登报寻人,把能找到的老兵,一个个拢到一块儿。 接着,把压箱底最后当年嫁人时穿的织锦缎旗袍,送进了当铺! 她拿着当来的钱,在贫民窟里,租了个通铺房。 好家伙,四十来个缺胳膊少腿的老兵,挤在二十平米的地界儿。 那日子,苦得没法说!可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啊! 凌维诚为了生计想到了新办法,牵头弄了个“孤军工业服务社”,想让老兵们靠自个儿的手艺,糊个口。 可兵荒马乱的,哪有那么容易? 眼瞅着要入冬了,老兵们挤在那小破屋里,冻得直哆嗦。 凌维诚愁得整宿整宿睡不着。 正没抓挠的时候,上海解放了! 陈毅当了新市长。 凌维诚心想也不知道这新政府认不认他们这些“国军”的老黄历。 可为了老兵们能活命,她找来张糙纸,给陈市长写了封信。 信里头没诉苦,没喊冤,就一句话,替那些活着的“死人”求个情。 这封信,最终送到了陈毅手里。 陈毅是谁?他咋能不知道谢晋元? 看着信,陈毅旁边的秘书提醒他,说吴淞路466号那栋小洋楼,是接收的敌产,按规定得充公。 陈毅一听:“充公?瞅瞅那墙上的枪眼!那是咱中国人的血性!就给凌维诚!给那些活着的英雄!” 陈大市长拍板吴淞路466号,就成了凌维诚和孤军老兵们的新家。 房子是有了,可开头那档子“作风问题”的误会,也就跟着来了。 凌维诚把找到的老兵,陆陆续续都接进了466号。 老兵们都是青壮汉子,虽然身上有伤,可模样还在那儿摆着。 一群大老爷们儿,跟着个寡妇住一块儿,街坊们肯定直泛嘀咕? 风言风语一起,举报信就递上去了。 派出所的民警奉命来查,屋里头的老兵们,没一个慌的,也没一个争辩的。 他们默默地,从衣裳口袋里,掏出“524团1营”的旧证件,有生锈的孤军纪念章,还有那张印着四行仓库授勋的老照片。 东西往那儿一摆,带队的民警,眼圈“唰”一下就红了! 打那以后,吴淞路466号,再也没人嚼舌根了。 小院的后院搭起竹棚子,独臂的老兵,摇着纺车织袜子。 腿脚不利索的,就坐着板凳,给火柴盒贴磷纸。 凌维诚把自个儿当年嫁衣上抽下来的金线,一针一线,绣在毛巾上,弄出个“孤军牌”! 她还琢磨个绝的,每块肥皂出厂! “孤军牌”的毛巾、肥皂一上市,虹口的菜市场排起长龙! 这466号小院,成了老兵们最后的营盘,也成了凌维诚践行诺言的地方。 凌维诚用她这一辈子,守着当年对男人、对那些兵的承诺,把一段差点被乱世吞没的悲情往事,愣是改写成了响当当的忠义传奇! 主要信源:(《陈毅在上海:1949-1957》——上海人民出版社)#头号创作者激励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