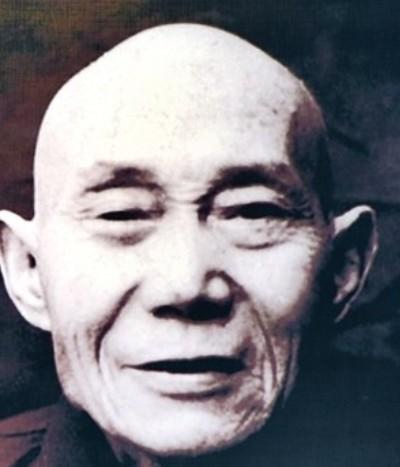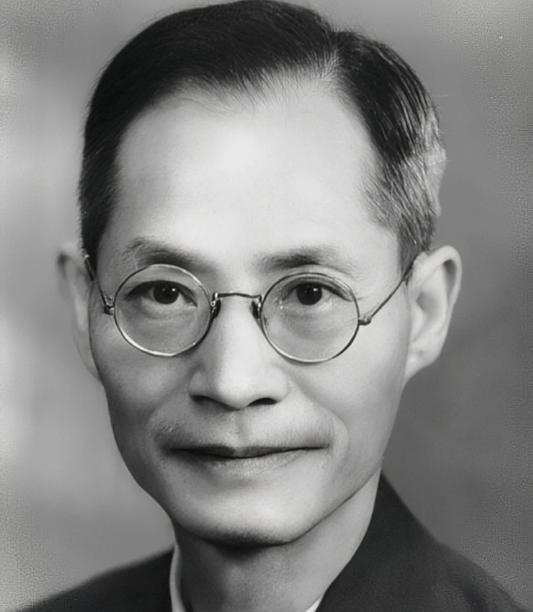1928年年初,30岁的程儒香被敌人拖到箭厂河吴氏祠堂大门外,一阵毒打后,被扒光衣服后拉开四肢,用四根铁耙齿钉把他四肢钉在清砖墙壁上,殷红的鲜血,咕咕的流淌,钻心的剧痛,使他在寒冷的冰天雪地里额头上冒出豆大汗珠,一阵阵疼痛的抽搐,汗珠如雨一般滚落。 1928年初。地点,河南、安徽、湖北三省交界的大别山区。冰天雪地,一个活生生的人,被当成一张“画”,用铁钉“挂”在墙上。 这是多大的仇,多深的恨? 其实,对于那些恨他入骨的敌人——当地的地主武装“红枪会”和民团来说,这不仅仅是仇恨,更多的是恐惧。他们在恐惧程儒香这个人,更恐惧他所代表的那股力量,那股能让穷苦人挺直腰杆子、敢于反抗的“精气神”。 杀人有很多种方式,一颗子弹就能解决。但他们偏不。他们要用最残忍、最羞辱的方式,把他钉在墙上“示众”。他们要让所有人都看见:“这就是跟我们作对的下场!”他们要用程儒香的血,浇灭老百姓心里刚刚燃起来的火苗。 然而,他们算盘打错了。 程儒香在被钉上墙壁,生命进入倒计时的时候,他没有求饶,也没有哭喊。他用尽最后的力气高喊:“共产党万岁!苏维埃政府万岁!” 这声音,在寒风里,估计传不了多远。但在场看到的每一个人,无论敌我,我想,一辈子都忘不了。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能让一个人在肉体承受极限痛苦时,依然坚守着内心的呐喊? 咱们现在是2025,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一个物质极其丰富的时代。我们讨论的是下一代AI会怎样改变世界,是马斯克的星舰什么时候能载人去火星,我们很少会去想,一百年前,有一个叫程儒香的年轻人,为了一个他可能完全看不到的“新中国”,把自己永远“钉”在了一面墙上。 有人可能会说,聊这些有啥用?太遥远了,跟我们有啥关系?关系大了。 前段时间有一个新闻,说是大别山革命老区,就是程儒香烈士战斗和牺牲的地方,这几年搞“红色文旅”,发展得特别快。特别是进入2025年以来,一条新修的“红色旅游高速”全线贯通,把当年红军战斗过的那些零散的旧址、纪念馆都串了起来。很多年轻人,开着新能源车,带着孩子,利用周末去实地走一走,看一看。 其中有个细节,说是在箭厂河的吴氏祠堂,也就是程儒香牺牲的那个地方,当地文旅部门在2024年底启动了一个“数字复原”项目。他们通过高精度的3D扫描和VR技术,让参观者能“身临其境”地感受那段历史。 当戴上VR眼镜,看到那个虚拟的场景时,心里咯噔一下。屏幕上模拟的雪花,耳边呼啸的风声,都比不上墙上那几处模糊的、据说就是当年钉痕的印记来得震撼。 支撑程儒香的,到底是什么?” 是一种信仰,在程儒香他们那一代人心里,信仰是实实在在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他们的信仰是什么?是“苏维埃”,是“新中国”,是“人人有饭吃,有衣穿”。这个目标,在当时看来,遥远得就像个神话。为了这个“神话”,程儒香和他的战友们,领导了著名的“商城起义”。他们一度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让穷苦人第一次当家做主。 虽然起义最后失败了,但它像一颗火种,点燃了整个大别山。程儒香的牺牲,没有浇灭这团火,反而让它烧得更旺。他的血,浸透了那面墙,也“染红”了后继者的旗帜。 这就是信仰的力量。它能把一个人的血肉之躯,变成一座精神的丰碑。 程儒香的故事,最打动人的是他那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决绝。在当时那种白色恐怖下,革命是九死一生。他知道,但他还是去了。因为他相信,他今天的牺牲,能换来一个他看不到,但后人一定能看到的、光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