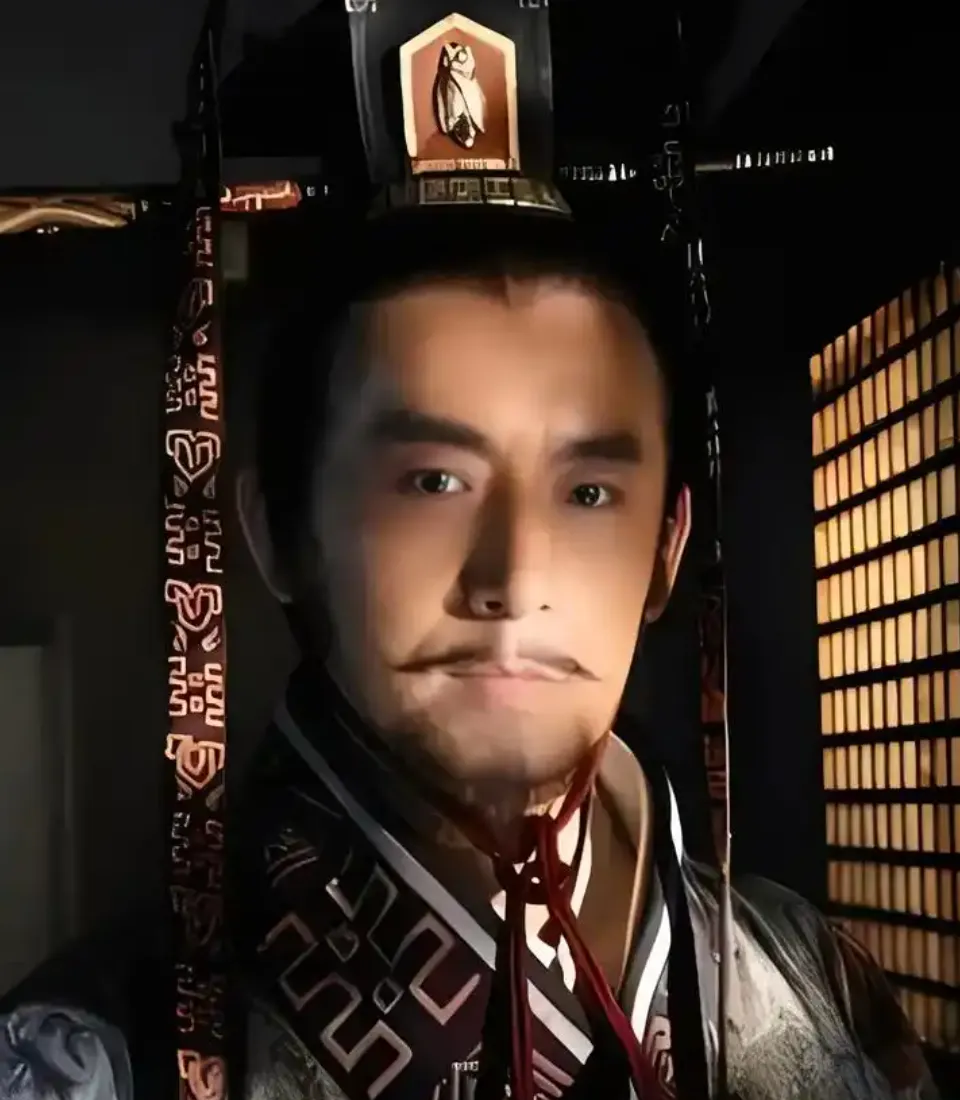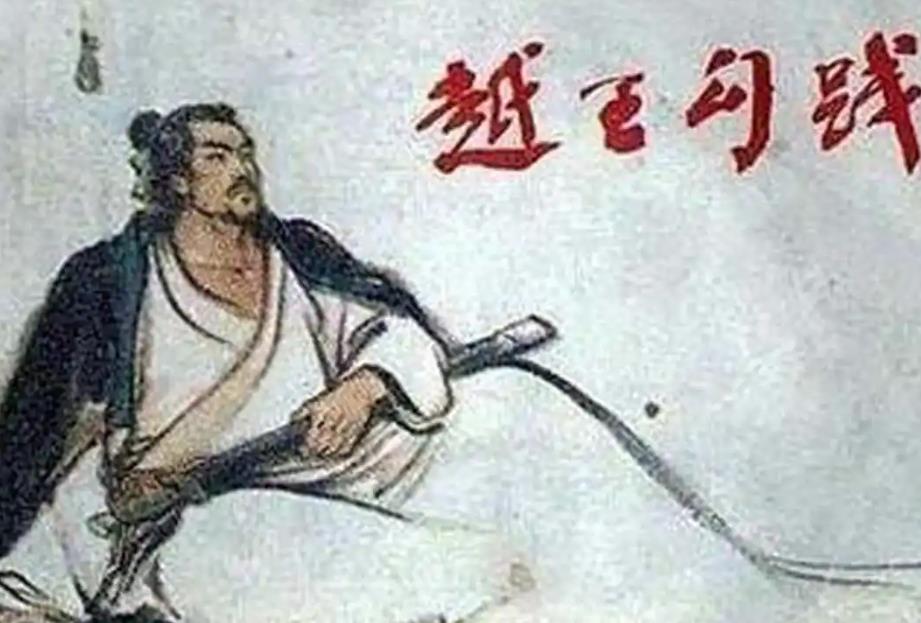夏朝末年,商汤迎娶有莘国君王的女儿为妃,并对有莘氏的奴隶伊尹说:“我是为了要你,才不得不娶的她。” 这句话像块烧红的铜,烫得伊尹手里的陶罐差点落地。他低头看着自己黥过的手腕——奴隶的印记还泛着青,可商汤的眼神比祭坛上的圣火还烈,仿佛他不是个端锅的庖人,而是藏着九鼎重器的宝匣。 迎亲的队伍在洹水边歇脚时,有莘氏的公主正对着铜镜描眉。她鬓边插着的玉簪,是汤让人连夜从玉石矿里赶制的,可陪嫁的奴隶里,只有伊尹被允许站在篷车边。汤的侍卫偷偷塞给伊尹块麦饼,“主公说,让你垫垫肚子,夜里还要议事。” 麦饼的热气混着河风扑过来,伊尹忽然想起昨天在有莘国的厨房,他正给公主炖鹄羹,汤的使者就掀了帘子进来,“我家主公说了,只要你肯走,这门亲事就算定下了。” 新婚之夜的红烛噼啪作响,汤却在偏殿翻着夏桀的税册。伊尹捧着炖好的雉羹进来时,正撞见汤用刀在竹简上划“桀”字,木茬子溅得满桌都是。“夏朝的粮仓在洛水南岸,可农夫连糠麸都吃不上。”汤抬头时眼里带着血丝,“你在有莘国见过夏使催贡,那些人是不是总说‘天子食九鼎,百姓当输粟’?” 伊尹把羹碗放在案上,忽然解开上衣。后背上纵横的疤痕在烛火下像幅地图——那是去年夏桀的人来有莘国催征,他替老弱求情挨的鞭子。“主公你看,”他指着最深的一道,“那天他们把孩童绑在车辕上,说不交粮就沉河。百姓跪在泥里哭,可夏使还在帐里喝我们的酒。” 汤的手指抚过那些疤痕,指尖抖得厉害。他想起十年前去夏都朝见,亲眼见桀把饿殍的骨头当柴烧,还笑着对诸侯说“这火比祭祀的还旺”。那天回来的路上,他在黄河边立誓,若不能解民倒悬,甘愿被鱼鳖分食。 有莘氏的公主不知何时站在门口,手里攥着块玉佩。那是汤送她的聘礼,上面刻着“永结同好”。她看着两个男人在烛下低语,忽然把玉佩放在案上,“我爹说,夏朝气数尽了。你们要做什么,不必瞒着我。”汤抬头时愣住了,公主已转身往外走,“厨房还有些豆豉,是伊尹家乡的做法,我去取来。” 三个月后,伊尹以陪嫁奴隶的身份随公主入商。汤在宗庙祭祖时,故意让他捧着鼎俎站在诸侯面前。有个从夏都来的使者嗤笑:“商侯竟让奴隶登堂,不怕上天降罪?”汤没说话,伊尹却举起鼎俎朗声道:“天生民而立君,君若残民,不如奴隶。”话音刚落,满殿诸侯竟无一人反驳。 夜里议事时,汤总让伊尹坐在自己身边。案上摊着夏国的地形图,伊尹用烧红的铜针在“鸣条”的位置烫了个洞,“这里是桀的粮仓,也是他的软肋。我们先断其粮道,再以‘天命诛暴’号召诸侯,必胜。”汤看着那冒烟的小洞,忽然想起迎亲那天,伊尹在车辕上刻的那句“民为水,君为舟”。 公主偶尔会来送宵夜,总带着伊尹爱吃的麦饼。有次她听见两人在说伐夏的日期,竟从妆匣里取出个锦袋,里面是有莘国的兵力布防图。“我爹让我转交的,”她脸上泛着红,“他说,商侯若能救万民,有莘国愿为前驱。”汤接过锦袋时,发现里面还有块绣帕,上面是公主绣的禾苗,根须扎得密密麻麻,像极了伊尹说的“民心如根”。 决战前一夜,汤在军帐里占卜。龟甲裂纹显示“大吉”,可他还是睡不着。伊尹煮了锅小米粥进来,“主公还记得那句‘我为你才娶她’吗?”汤笑了,“怎么不记得,那时你还瞪我,好像我说错了什么。”伊尹也笑,“现在才明白,主公娶的不只是公主,是天下的民心。” 第二天清晨,商军在鸣条列阵。汤站在高车上,看着对面夏桀的军队里,有士兵偷偷往这边扔来夏国的税册。伊尹捧着象征天命的玄圭站在他身后,忽然听见身后传来马蹄声——有莘氏的公主带着娘家的军队来了,银甲在阳光下闪得耀眼。 战后论功,汤要封伊尹为相,有人反对说“奴隶不可为卿”。公主却捧着传国的九鼎走出来,亲手将最沉的那只放在伊尹面前,“当年商侯为他娶妻,今日我为他举鼎。谁不服,先问问这鼎答应不答应。” 伊尹摸着鼎耳上的饕餮纹,忽然想起夏朝的厨房里,他曾给桀炖过无数次羹,可那些珍馐里,从来没有百姓的味道。而现在,商国的鼎里煮着新收的小米,香气能飘到十里外的村落。 参考书籍:《史记·殷本纪》《墨子·非攻下》《吕氏春秋·本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