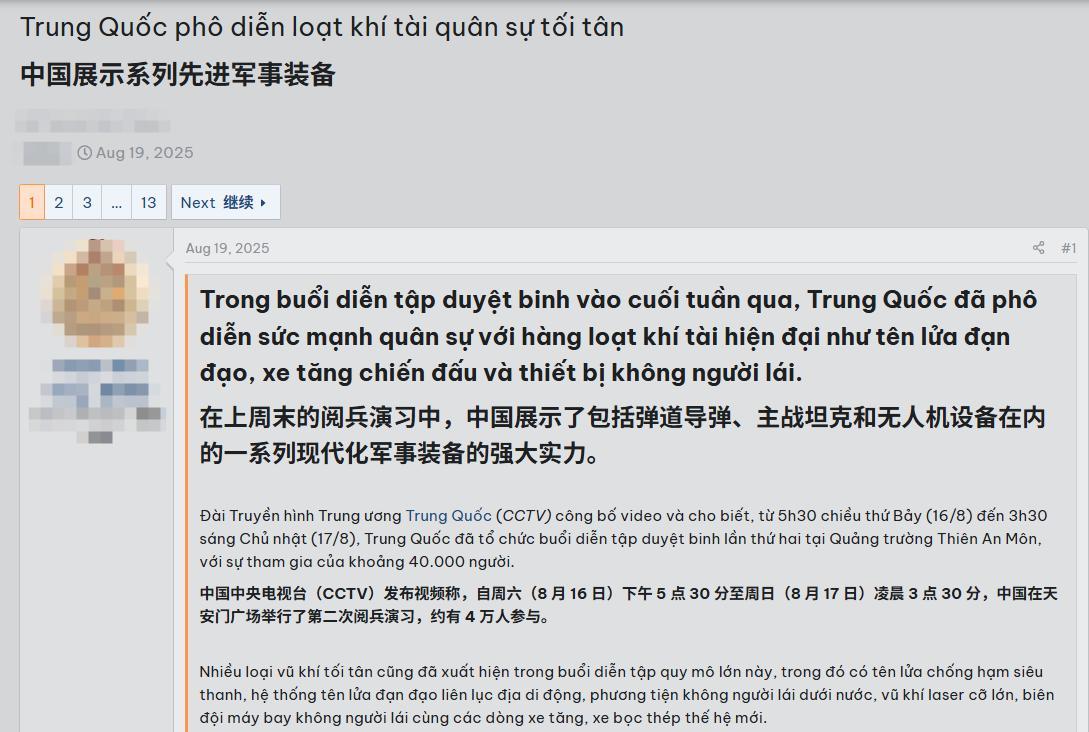一位参加过两山轮战老兵回忆,来偷袭我方阵地的越军特工很狡猾,他们只穿条裤衩,光着四肢爬行,碰到地雷,皮肤能感觉到,动作也很轻,使我们防不胜防。 越军特工的手段,说起来真让人头皮发麻。 那些人夜里不穿军装,也不背枪械哐啷作响,就一条裤衩,四肢紧贴着泥地往前爬。那姿势你想一想,像蛇,又像蜥蜴,身体和土地合为一体,安静得连草叶被压弯的声音都微弱得听不清。 他们把皮肤当探测器,土里埋着地雷,稍一不对劲,手掌和腿肚子能感觉出来,立刻停下。 很多次,我军前哨根本没听见脚步声,就发现鼠群惊慌逃窜,这才知道有东西逼近。你要说狡猾吗?确实狡猾。白天打仗靠炮火,夜里拼的是胆气和心跳,这些特工就是专门钻人的神经空子。 可是,说到最难熬的,并不只是他们,而是那一口口猫耳洞。 天然的溶洞挖出来,黑咕隆咚的,只能蹲只能蜷缩。 几个人肩膀抵肩膀挤在里面,汗水和呼吸交织得像雾气。温度四十度以上,潮气不散,衣服紧紧糊在身上,不出几天皮肤烂开了口子,生脓,发臭。有人干脆不穿衣服,光着身子挤着坐。 领导到前线看见过,一群年轻人赤条条地跑出来,尴尬得笑,解释说这是为了透气,不然就要烂掉。你说残酷吗?真残酷。 雨季更像噩梦。水从洞口哗啦啦地灌进来,士兵们用头盔拼命往外舀,可雨一连下好几天,水位越来越高,人整夜泡在水里,脚指头肿得发白,皮肤皱得像老树皮。 积水不是清水,里面漂着粪便、油污,死鼠浮在水面,蛇从石缝里钻出来。 有人静静靠在洞壁上,腿边忽然一阵冰凉,是条蛇正要绕过去。你不能乱动,只能屏住呼吸,等它离开。等雨停,水慢慢退下,新的问题马上来了——渴。 那时候,水比粮食还珍贵。 运不上去,只能靠天。洞里的人嗓子干得冒火,开口说话声嘶哑。 夜里,把雨衣摊在外面,等第二天早晨舔几口露水,算是润嗓子。撤回后方的士兵,有的抱起水壶猛灌,灌到胃里翻江倒海,还舍不得停。想象一下,那是怎样的渴。 猫耳洞的另一种常客,是蚊子。越南的蚊子个头大得出奇,扑过来像小鸟拍翅,咬一口留下鼓鼓的红包,痒到发疯。白天夜里没区别,你身上满是疤和包。 士兵们索性编打油诗,把折磨写成笑话,说“越南的蚊子大如鹅”。 他们用夸张的笔调讽刺现实,笑声短促,却能把压抑的空气撕开一道口子。至于老鼠,遍地都是。 它们钻进背包,咬断鞋带,啃掉耳朵。有人半夜醒来,血淌一脸,耳廓被啃掉了一块。可同样的老鼠,也成了伙伴。 战士们在阵地前撒点粮食,看老鼠的动向。要是忽然集体逃窜,多半是敌人摸上来了。 于是,老鼠被叫作“活警报器”。有人更大胆,绑罐头盒在老鼠身上,点燃尾巴,让它们乱窜。越军以为有突袭,惊慌失措,自己对着黑暗开火。 这种法子听起来荒唐,可在猫耳洞里,它是妙计。 潜伏最怕瞌睡。人困到极限,眼皮像千斤重,偏偏这个时候最危险。老兵说过,他们甚至感谢蚊子。叮得钻心生疼,倒是让人瞬间清醒。 风雨的夜里,冷风钻进衣领裤脚,冻得骨头发麻,身体僵硬,也不能动。周围静得只剩彼此的呼吸。等到天亮,敌人没来,留给士兵的就是满身红肿的疙瘩。 具体的战斗,比这一切更凶险。老山和法卡山的山洞里,越军火力密集。想过,就得清除。一次,发现山顶溶洞藏着敌人几十人,机枪、冲锋枪对外喷火。正面硬攻,就是送命。一个河南小伙子站出来,黑白分明的眼睛亮得吓人,他说他去。 洞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岩壁上青苔湿滑,石笋锋利,擦着皮肤就是血痕。 背上的包太碍事,他干脆扔下,轻装钻进去。枪声突兀响起,子弹擦着帽檐飞过,他扑过去,双手死死掐住敌人的脖子,直到那人没了气息。炸药点燃,火光照亮整个洞穴,烟雾呛得人睁不开眼。敌人乱作一团,最后整个洞口化成火海。年轻的脸上全是烟灰和血迹,他自己也分不清哪些是敌人的。 战争是地狱,猫耳洞是地狱里的地狱。 可是,在这样的炼狱里,人还是人。有人在泥水里舔露水活下去,有人在黑暗中用老鼠对抗敌人,有人在逼仄的空间里写打油诗自嘲。 他们没有被彻底摧毁,反而留下了最倔强的身影。 多年以后,老兵回忆起来,说自己那时整夜蜷缩,身边全是呼吸声和皮肤溃烂的味道。半夜醒来,摸到洞顶滴下的冷水,忍不住伸出舌头去接。那一瞬间,他觉得自己活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