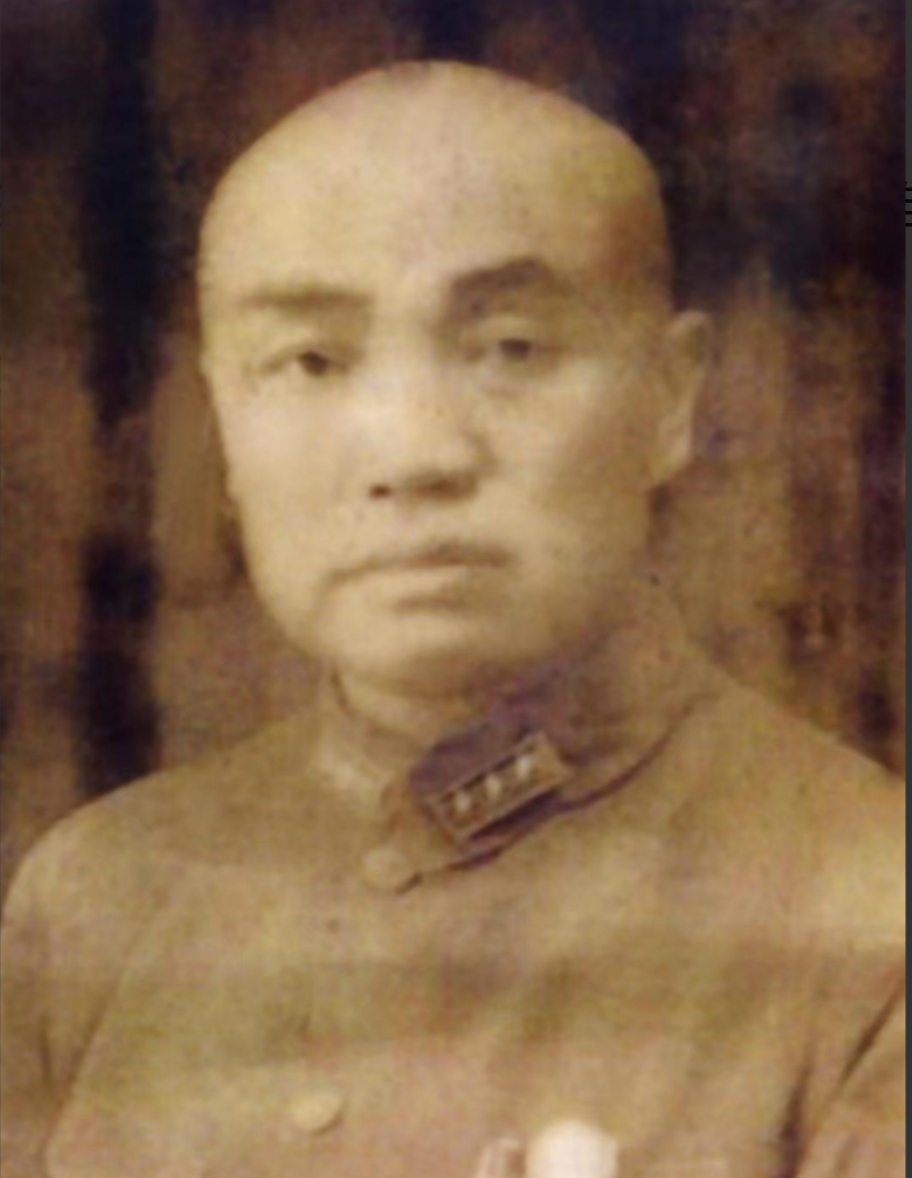1918年秋,毛泽东五十二岁的生母文七妹脖子上长了一个包。不久以后包上溃烂了一个洞,滋滋地往外冒着血水。
1918年秋天,文七妹脖子上突然长了个包,一开始没当回事,以为是劳累上火啥的。可没多久,包肿起来,表面破了个洞,血水往外冒,声音还挺渗人的,滋滋响。那个年代医疗条件差,农村更没啥好大夫,她就自己用布裹着,忍着疼继续干活。家里人看她越来越虚弱,毛泽民和毛泽谭两个弟弟商量着,得带母亲去长沙找大哥毛泽东瞧瞧。来年春天,1919年4月左右,病情重了,脖子肿得厉害,吃东西都咽不下去。毛泽民扛着行李,毛泽谭扶着母亲,从韶山冲出发,一路颠簸去省城。
长沙那时是湖南中心,毛泽东在那儿教书,顺便参加些社会活动。他接到弟弟们护送母亲来,赶紧安排住处,然后带去湘雅医院,那可是当时长沙最好的西医医院,由美国人办的,设备相对先进。医生检查后,说是淋巴腺炎,结核性的,在那个医疗水平下,基本没治。文七妹看了几回大夫,吃药打针,效果不明显,她自己也知道情况不好,坚持要回老家韶山冲。毛泽东兄弟仨见母亲这样,挺难受的,就想着留个念想,领着她去溁湾镇的照相馆拍了张合影。这是文七妹头一回照相,照片上她坐在中间,儿子们围着,那张照片后来成了珍贵的纪念。
文七妹回家后,病情没好转,夏天过去,秋天又来,10月5日,她在韶山冲自家床上走了,享年53岁。毛泽东那时不在身边,弟弟毛泽覃陪着,他听到消息,带着毛泽覃赶回老家,母亲棺材已经封了两天。他跪在灵前,写了生平最长的一首诗,叫《祭母文》,诗里念叨母亲一辈子辛苦,生七个孩子,养大三个儿子,表达了对母亲的感激和悲伤。
文七妹的病,在当时真是常见又无奈的事。淋巴腺炎多半是结核杆菌引起的,农村卫生差,营养跟不上,容易得这种病。那个年代抗生素还没普及,治疗靠休息和中药,西医也有限。毛泽东后来回忆母亲时,总觉得遗憾,要是搁现在,肯定能治好。1959年6月,他重回韶山,走到父母坟前,放了把松枝,低声念“前人辛苦,后人幸福”,然后对身边人说,当年母亲的病,现在医疗发达了,准能医好。这话挺接地气的,反映出时代变迁,医疗进步让普通人受益。
文七妹一辈子就是个普通农妇,没啥文化,但她养育的儿子们后来干了大事业。毛泽东对母亲的感情深,影响了他的人生观。他小时候,母亲教他念书识字,还支持他出去求学,不像父亲毛贻昌那么严厉。毛贻昌脾气大,爱打人,文七妹总在中间调解,护着孩子。这家庭环境,让毛泽东从小就懂了底层人民的苦,也养成了他坚韧的性格。文七妹信佛,吃素,家里穷她也乐善好施,村里人说她心善。她的离世,对毛泽东打击不小,那之后他更不想回家,专心在外头搞活动。